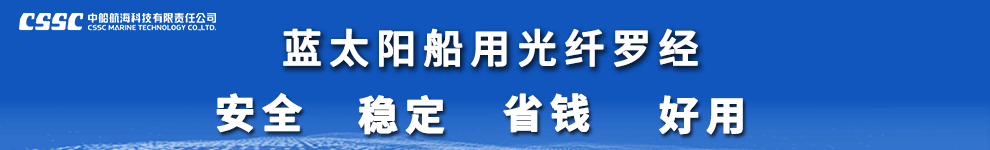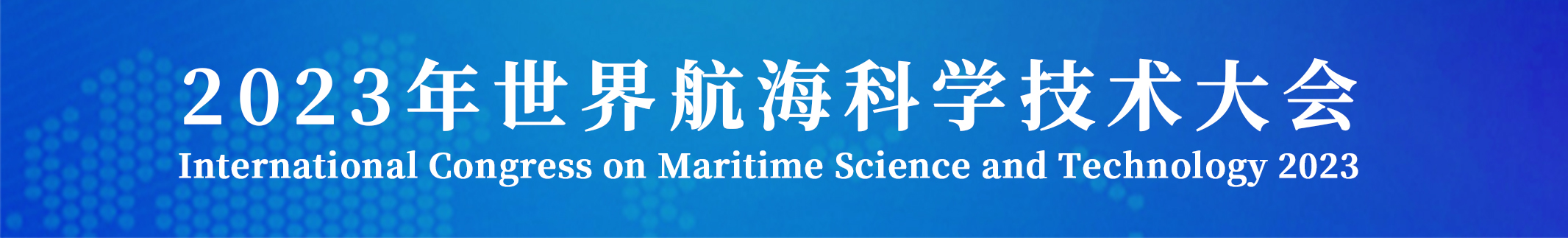北欧海盗 【史略】
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获胜的野蛮人也同样被基督的福音迷住了。虽然他们并不比今天的善男信女更能克制自己的邪欲,但是他们有共同的教义和神灵的启示。一条纽带联结着欧洲各个民族。一个世界性机构遍布所有国家,它无比强大,而且是罗马时代幸存下来的唯一的成为系统的机构。这一机构的首脑是罗马的主教,他在精神上或者至少以教职的形式,恢复了罗马皇帝已经丧失的权威。基督教会成了知识和学问的唯一庇护所,它的侧廊和回廊里收藏着从古代世界抢救下来的一切遗产。它使人们在冲突和罪恶中体会到,“人间悲哀得到唯一的安慰,尘世权力受到唯一的限制。”在异教文化的光辉尚未完全消失之时,新的光辉已经开始照耀野蛮人。不仅在我们的岛上是这样,在整个欧洲也都是如此。基督的启示驯服了野蛮人,并使他们精神振奋。从幼发拉底河 [ 译者注:在伊拉克境内。 ] 到博伊思河 [ 译者注:在爱尔兰共和国境内。 ] ,原来崇拜的偶像弃如敝屣,而基督的传教士则可以行迹四方,他们在每一座城镇都有心心相通的同教兄弟,都可受到普遍的热情招待,尽管这种招待有时是比较简朴的。
在罗马帝国的衰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轻视学术,所有知识分子起初都到教堂里躲避起来,后来他们从教堂里发挥出控制社会的力量。教堂成为培养政治家的学校。教士们实际上垄断了知识和写作技巧,因而那些傲慢专横的酋长们离不开他们。(小鼠:如果日耳曼的君主开科举士的话,或许就不会有那么庞大的教权,甚至基督教本身有可能走向衰落。谁垄断了知识,谁就掌握了未来啊。)教士成为各国王朝的官员,有些成为同家的栋梁。他们自然而且必然地成为罗马时代的地方行政官,穿着罗马行政官的服装。现在的教士还穿着这种服装。胜利的野蛮人不知不觉地屈服于一种机构。许多事例证明,他们依靠这种机构在无休止的权力之争中取得了胜利。在中世纪的动荡局面已经结束而阳光终于重新照耀到不列颠岛的时候,她醒了过来,发现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这世界既不减当年的仪表,也不失旧日的尊严,岛上的习习微风也更加令人心旷神恰。
新皈依基督教的异教徒的热情引起一些危害,这些危害造成了新的灾难。基督教根据自己的原则必定要反复灌输和善、宽容的思想。它的利益和教徒的热情使它必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权力结构。不久,入侵者的后代由于谦卑和虔诚而显得意志薄弱,受到有组织的盘剥。由于六、七世纪的这种盘剥,教会在许多国家占有财产和土地的数量之大,简直超过了它控制局势的需要。当时基督教世界有虔诚的信仰,然而也是难以控制的,它在精神上获得了统一,却苦于俗界的纷争;它得到神的感化,但也受到了权欲野心的威胁。
此时,在这个刚刚苏醒、处于恢复时期的松散社会里,又刮起两股外来侵略的冷风。一股风来自东方,在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举起了伊斯兰的军旗和圣旗。六二二年,他从麦加逃到麦地那,这次著名的事件素称“徙志”,穆斯林纪元就是从这时开始计算的。在随后的数十年里,穆罕默德和继承他的哈里发们 [ 译者注: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继承人的尊称,是伊斯兰教政教合一的领袖。 ] 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半岛、波斯、拜占庭帝国的许多地方以及北非的所有沿海地区。八世纪初年,伊斯兰教传过了直布罗陀海峡,盛行于西班牙,直到大约八百年以后才被清除出去。法国一度似乎也要投降,但是在七三二年,查理大帝的祖父查理·马特在普瓦蒂埃一带打败阿拉伯人,把他们赶了回去。所以说,伊斯兰大军几乎打到了不列颠群岛。
还有第二股入侵的冷风在等着款待不列颠。这次入侵来自北方,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海盗准备好了细长的船只,要破浪南侵。在阿拉伯开教徒和北欧海盗的两面夹攻下,本来已经衰落的欧洲社会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不得不分力对付他们。直到十一世纪,中世纪后期基督教世界的封建骑士们(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是皈依基督教的北欧海盗后裔)才完全阻上了阿拉伯人的前进,在基督教的阵营中形成了庞大而有力的军事力量。
* * *
一报还一报。撒克逊海盗对布立吞人所做的一切事在四百年后轮到了他们自己的头上。八世纪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对外征伐的欲望产生了强大的力量。挪威、瑞典和丹麦派出一股股可怕的武装力量,这些人不仅骁勇善战,还能顽强地同风浪搏斗,在苍茫的大海上任意东西。这些民族之所以要对外侵略,进行冒险活动,是因为他们的力量和人口同时增长,还因为各国王室之间进行着错综复杂的斗争。当时,这些北欧人并未遇到由于来自亚洲平原的新压力而被迫西迁的问题,他们是自动进攻的。这些北欧人勇猛惊人,其中有一股军队从瑞典挥戈南进,不仅打到君士坦丁堡,而且在那里撒下了在几个世纪里影响俄国欧洲地区的茁壮种子。另一部分人乘着他们的长船从挪威到达地中海,骚扰沿岸各国,同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和非洲北部沿岸建立的一些王国进行激烈的较量之后,败退下来。第三股斯堪的纳维亚海盗直奔不列颠群岛、诺曼底和冰岛,不久又穿过大西洋来到美洲大陆。
丹麦人同挪威人的关系错综复杂,变化无常。他们有时狼狈为奸,有时又互相残杀,但对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却是共同的威胁。他们极端残忍,虽然不吃人肉,却经常在胜利后聚餐时,在敌人的尸体上架起锅灶,有时甚至把锅直接放在尸体上。在挪威人和丹麦人在爱尔兰进行一次战斗以后,采取中立态度的爱尔兰人对这种可僧的习惯表示厌恶,他们问这些北欧人为什么这样做,得到的回答是,“为什么不呢?他们要是打胜了,也会这样对待我们的。”据说,这些斯堪的纳维亚猎人从来不为自己的罪过而哭泣,也从来不为同伴的死亡而落泪。不过,他们在许多地方一旦定居下来,就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他们洗澡,穿丝绸礼服。他们的船上还携带着上岸后要用的帐篷和床铺。在他们侵入的各个地方,他们的军事首领都享受多妻制,在东方甚至照搬了宫妃制。据说,有一个首领在征服异地之后所占有的妻妾不下八百名。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受了《圣经》故事的影响。九三六年利默里克城从北欧海盗手里夺回来的时候,他们住宅中女人的花容月貌以及她们身上的刺绣别致的锦衣丝带,使爱尔兰人神魂颠倒。当然,这些爱尔兰人很快就又神态自若了。
* * *
北欧海盗依靠的主要是他们的长船。他们不断改进这种船,使它在八、九世纪臻于完善。这种船吃水浅,可以沿河逆流而上,能在许多溪流和港湾里停泊,这种船由于有合适的形体和柔韧的结构,能够安然经受大西洋上最强烈的风暴。
我们对这种船只已有较多的了解。有六只船完好无损地发掘出来了,其中最著名的是一八八〇年在挪威格克斯塔德的一座古冢中挖出的那一只。这只船上的东西几乎样样俱在,甚至包括水手的饭锅和跳棋盘。一九四四年虽是多事之秋,人们还是把这只船重新精确地量了一遍。它的长度是七十六英尺六英寸,宽度是十七英尺六英寸,中部吃水仅二英尺九英寸。它的两边各由十六条硬橡木做成的列钣叠接起来,用木栓和U形铁钉钉牢,船板之间的空隙用编成辫子的兽毛堵塞起来。船板用有韧性的植物纤维做成的绳子绑在肋材上,因此船体具有颇大的顺应性。甲板的木板都是活动的。补给品无疑是装在贮存箱里,但是这些贮存箱已经不见了。它的桅杆立在巨大牢固的桅座上。科林伍德教授说,桅杆立得非常巧妙,“当它挺立而起的时候,轻而有弹性的船体不受任何拉力的影响(我把他的话改写成现代英语了)”。船上有十六对桨,桨形优美,长度一般在十七英尺到十九英尺之间,长桨用在船头和船尾,因为这两处船舷的上缘离水面高些。桨孔打在船舷的主要外钣上,孔上有一块木板帘,桨收进来时可以把孔堵上,舵装在船尾右舷,形状象网球拍,其实是一个粗大的短桨。舵柄是活动的,安装的形式很巧妙,使舵叶便于活动。桅杆高四十英尺,一根又长又重的帆桁挑着一块方帆。这只船还可以携带小舢舨,我们发现了它的三只小舢舨。在格克斯塔德发现的这只船可带五十名船员,必要时还可以另带三十名战士或俘虏,不管天气如何,它能在海上活动一个月之久。
北欧海盗就是乘着这类大小不同的船只去掠夺文明世界的。他们乘船去攻打君士坦了堡,围困巴黎,建立都柏林,发现美洲。现在我们可以生动而清晰地描绘出这类船只的图景:龙首船头,精雕细刻,船尾高高翘起,船旁排着黑黄交错的盾牌,刀剑寒光闪闪,显得杀气腾腾。用于远洋航行的长船则更加坚固,干舷也更高一些。一八九二年,按照格克斯塔德的船型仿造了一艘船,挪威人驾驶这条船横渡大西洋,而且只用了四周的时间。 (小鼠:哥伦布泪流满面了啊。。。)
然而,海上军事力量所依赖的这种高级工具要是没有人来掌握,还是一堆废物。掌握这一工具的人都是自愿而来的,他们的头领非常能干。在中世纪的北欧传说中,我们读到了有关船上这些“斗士或欢乐之人”的情况:船员无疑是从许多申请者当中挑选出来的,他们“掌舵和划桨正象使用刀剑一样熟练”。他们一加入海员的队伍,就得遵守严格的纪律——早期的“军事法规”。参加者年在十六岁到六十岁之间,每人都得经过体力和敏捷程度的测验。在出海或从戎期间,谁也不许心怀旧怨。船上不得携带女人,发现情况时只向船长一人报告。所有的战利品都得集中到火刑柱前,在那里出售或者按照规定分配。战利品只属于个人,也就是说,根据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法律,一个人的战利品不得遗留给他的亲属。但是他有权把这些东西带入坟墓。
奥曼写道:“对付数量相等的敌人,北欧海盗总能保持不败。但是,当整个乡村都发动起来,许多郡的人民一齐起来反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得当心,否则,就有可能被众多的敌人所消灭。”北欧人只有与非常庞大的舰队同来的时候,才敢和敌人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这些侵略者东抢西劫,却不善于打仗,只要发现岸上有强大的守卫者,就回到船上,驶到没有被掠夺过的省份,洗劫一番。此外,他们很快掌握了在陆地上的机动能力。他们一登陆,就立即搜罗附近的马匹,带着掠夺品骑马东奔西窜。他们搜集马匹并不是为了打仗,而只是为了决速运动。公元八六六年首次提到英格兰境内乘马劫掠的做法。那时“野蛮人的大军来到东撒克逊人的土地上,而且是骑马的军队。” [ 原注:引自公元八六六年出版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 ]
他们的无耻行为不亚于任何其他海盗,但是我们考虑他们的暴行时,也不要忘记他们的严格纪律、刚毅精神、亲密关系和军事特长。他们就是靠着这些特点横行天下,成为当时最令人生畏的勇敢民族。
* * *
大约在七八九年夏季的一天,当“纯正无邪的英格兰人在安谧的气氛中走向田野,把牛套在犁上”时,国王的官员、多尔切斯特的地方长官接到报告说,有三艘海船已经靠岸了。地方长官以为来客是商人而不是敌人,便“跳上马,带着几个人赶到港口(很可能是波特兰港)。他以长官的口气下了命令,要把来者送到王府去。但是,来者当场杀死了他和他的随从”。于是,一场残酷的斗争开始了,这场双方互有胜负的斗争折磨和蹂躏英格兰达二百五十年之久。它是北欧海盗时代的开端。
七九三年一月的一个早晨,诺森伯利亚沿海林迪斯法恩岛(也称圣岛)的一个富裕的修道院,受到一支强大的丹麦舰队的突然袭击。丹麦人大肆洗劫,宰了家畜,杀害了许多修士,带着大量的金银珠宝和圣徽扬长而去,还带走了能在欧洲奴隶市场高价出售的所有修士,这次袭击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海盗在隆冬时节呼啸而至,陆地上的任何援兵都无法及时赶到。这次暴行的消息四处传播,不仅传遍英格兰,也传遍了欧洲。基督教会向四方发出了警报。诺森伯利亚的阿尔克温从查理大帝的王宫里往国内写信,安慰他的同胞说:
嗨!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已经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生活了将近三百五十年,如今我们在异教徒手里受到了不列颠前所未有的可怕磨难。大家没有想到他们竟然会完成这样的一次航行。看看圣卡思伯特的教堂吧!它洒遍了基督教传教士的热血,礼拜用品被洗劫一空……波利纳斯离开约克以后,是这个教堂在我们中间撒开了基督教信仰的火种,但是痛苦和灾难也是从此开始的……在这场灾难之前出现过凶兆……那么四旬斋期间在约克发生的大惨案有过什么凶兆呢?
第二年,北欧海盗又来了。他们在贾罗登陆时碰上坏天气,受到了猛烈的反击,死了许多人。他们的“国王”被捉住后,处以极刑。幸存者逃回丹麦,细说这次惨败的经过,以致此后四十年里,无人再敢侵犯英格兰海岸。在此期间,北欧海盗不敢大规模出征,只是经常利用小股的海上力量袭击苏格兰东海岸和苏格兰的一些小岛。在那以前,这些岛屿一直是修道院的安全处所,如今修士们发现,他们成为特别易受攻击的对象。他们的财富和所居住的孤岛,使他们成为海盗眼中最诱人的猎物。爱奥拿岛在八〇二年遭到抢劫和破坏。爱尔兰的教会机构也成为贪得无厌的抢劫者心目中的稀珍。从那以后,当地教士不断蒙受苦难。教士的活跃力量和热情使教会在废墟上恢复了起来。北欧海盗在抢劫中有广泛的选择余地,因此他们第二次光顾某个地方时,那里已经有了一段恢复时期。爱奥拿岛就被洗劫过三次,基德尔 [ 译者注:爱尔兰的一个小镇。 ] 的一个修道院遭难不下十四次。
海盗活动成了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教会则是海盗的不断充实的宝库。查理大帝的御用历史学家埃京哈德记载道,侵扰劫掠连续不断,基督教世界笼罩在恐怖的阴影之中,无人能够采取有效的措施。而且掠夺的行当又如此多利,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人因此都看中了这个职业。一位苏格兰人笔下所称颂的“这些四肢优美、性格爽朗、骁勇善战的北国先生们”,每年都以更多的人数扬帆而来,满载而归。他们的收获使所有大胆无耻的老老少少都跃跃欲试。其他舰队的活动区域更加广阔,它们甚至进入了地中海。查理大帝在纳尔榜附近的一座小镇里,透过窗口望见了这些可恶的船只在沿海出没骚扰,令人难忘地预告了即将到来的怒潮。
* * *
八三五年,这场风暴终于席卷而来。有时拥有三、四百只船的舰队沿着河流驶入英格兰、法国和俄国的内地,进行规模空前的抢劫。在三十年的时间里,英格兰南方不断遭受洗劫,巴黎不止一次被围困,君士坦丁堡受到袭击,爱尔兰的一些港口城镇多次陷落,奥拉夫部下的北欧人还建立了都柏林。北欧人在他们征服的许多地区定居下来。瑞典人侵入俄国中部,统治河边的城镇,以禁止贸易的手段勒索赎金。来自更为寒冷地带的挪威人发现苏格兰的岛屿适合居住,于是他们使设得兰群岛、法罗群岛和爱尔兰殖民化了。他们到了格陵兰岛和斯通兰(即现在的拉布拉多半岛)。他们乘船驶入圣劳伦斯河,还发现了美洲,但是他们并不重视这一创举。
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北欧人没有在不列颠和法兰西建立长期的立脚点。直到八六五年,大陆上的抵抗暂时得到加强,丹麦人才开始大举入侵诺森伯利亚和英格兰东部。
此时撒克逊人的英恪兰果实已经成熟,可以挥镰收割了。入侵者在整个东部沿海一线扑上岛来。当年“撒克逊海岸伯爵”曾经保卫这些地区,可是此时,帝国时代留下来的工事已经沦为一堆瓦砾,被数百年的风尘残叶所埋葬了,再也没有罗马军队的战船荡桨巡逻,也没有罗马帝国政府派出的英明指挥官或罗马军团前来援救;有的只是遍布四方的大小修道院和教堂,它们在那个贫穷的时代拥有许多金银珠宝,还有大量的食物、葡萄酒和当时的其他奢侈品。虔诚的英格兰人囿于向教会捐钱才能免罪的观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经常忏悔,所以教会也就自然富足起来了。在这里,只要你拔出利剑,横财便随手可得。
除了过分服从教会之外,英格兰人当时还在军事方面处理不当。他们的防御体系只能将古代布立吞人的后裔限制在贫瘠的山区,或者防止邻近同族人的入侵。当地的贵族接到他的主人或国王的诏令时,可以把附近的强壮农民召集起来,就地服役四十天左右。这四十天的服役不是自愿的,期限一到,军队就解体了。至于敌人是否前进,或者他们自己刚刚进行的战斗是否已经达到目的,他们就不管了。现在他们面临的是另一种类型的敌人。丹麦人和挪威人不仅可以利用长期以来海上力量所提供的便利进行突然袭击,而且在陆地上也发挥了机动性和灵活性。他们还养成了每到一处就构筑营垒的习惯,这些营垒几乎象罗马人的营垒那样无懈可击。他们的谋略,尤其是他们惯用的“诈败”战术,备受赞赏。我们从史料中可以多次看到,英格兰人几乎击溃了这些异教徒,但是到了傍晚,丹麦人却能重新守住阵地。有一次,一批丹麦人围攻一个小城,他们的首领说他自己要死了,恳求当地的主教为他举行基督教的葬礼。这位诚实的主教很高兴有机会教化一名海盗,同意了他的要求。但是,当这位北欧人的尸体被抬入城里准备举行葬礼时,穿着丧服的随从突然变成了全副武装的精壮武士,他们不费吹灰之力,立即开始掠夺和屠杀。有关北欧人的作风和习俗的这类杂闻颇多。他们实际上是有史以来最大胆无耻、奸诈无信的海盗和骗子。由于撒克逊人的组织有严重的缺点和当时的客观条件,北欧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其实现的程度是任何仿效他们的人所望尘莫及的,而他们确有许多仿效者。
* * *
在这个时期的北欧传奇中,无人能比拉格纳·洛德布鲁克或“毛马裤”更有名了。他生于挪威,但是同丹麦的王族有关系。他年轻时就开始了海盗的生涯,“跨海征西”是他的格言。他的航海范围西抵奥克尼,东至白海。八四五年,他率领一支北欧船队沿塞纳河逆流而上,进攻巴黎。这次进攻被打退了,而且瘟疫也突然向海盗们进行了报复。他率领机动灵活的军队转而进攻诺森伯利亚,但他时运不济。据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他被诺森伯利亚的艾利国王俘虏,艾利国王把他扔进蛇坑,赐其一死。在一堆蜷曲蠕动、令人肉麻的蝰蛇中,他唱着歌迎接死亡。拉格纳有四个儿子,他躺在毒蛇当中时发出了灵验的威胁:“小猪们现在要是知道老公猪的遭遇,一定会哇哇叫的。”我们从北欧诗人的作品中,可以了解到拉格纳的儿子们听到噩耗时的反应。“勇士”比约恩紧紧地握着矛杆,指痕都印到上面去了。维特瑟克正在下棋,他死死地抓着一个小卒,鲜血顺着指甲流出来。“蛇眼”西格德正在用刀削指甲,他不停地削,直到削到了骨头。但是,第四个儿子“无骨人”伊瓦尔是不可小看的人。他叫人讲了其父蒙难的细节,脸色“忽红,忽灰,忽白,浑身要气炸了”。 [ 原注:引自J.A.哈默顿所编的《世界通史》(The Universal History of the World)第四卷。 ]
根据当地报仇的规矩,儿子应该向杀死他们父亲的仇人进行报复。仇人的肉和肋骨必须砍成或锯成老鹰形,然后,孝顺的儿子用双手掏出还在悸动的肺。这种报仇方法叫做“血红的鹰”。据传说,艾利国王就是落得这样的下场。它给英格兰造成的实际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无骨人”伊瓦尔既有军权而又诡计多端,是九世纪末年斯堪的纳维亚人入侵英格兰的指挥官。是他策划了征服东英吉利、诺森伯利亚的德拉以及默西亚的那些大战役。他以前一直在爱尔兰作战,但是在八六六年,他出现在东英吉利。他的强大军队本来是在船队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八六七年春天他却骑着马,沿着昔日的罗马大道向北挺进,乘船渡过了亨博河。他们骑马是为了加快行军的速度,而不是为了打仗。
他包围了约克。诺森伯利亚人由于分别忠于两个互相抗争的国王,长期处于分裂状态。这时他们忘记宿怨,联合对敌,要决一死战,但为时已晚。他们向约克城下的敌人发动了反攻,起初还算顺利,从城墙上把丹麦人打得向后退了一些,随后杀出城去。在混战中,丹麦人把他们全部击败,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将两位国王杀死,并且完全摧毁了诺森伯利亚的抵抗力量。诺森伯利亚王国的气数就此告终。英格兰北部再也没有恢复它的优势。
霍奇金有过这样一段记载:
学校和修道院都湮没无闻,或者根本不复存在了。这个王国出了毕德和阿尔克温这样的人物,它留下了石制的大十字架这样的英格兰艺术明珠,也产生了西德蒙 [ 译者注:公元七世纪的英格兰诗人,有“英格兰歌父”之称。 ] 的作品和《十字架显圣》这样的英格兰诗歌。但是它在八六七年惨败后的几十年里没落了,再度陷入黑暗的野蛮状态中……一个王朝覆没了,它的宗教几乎奄奄一息,它的文化又回到了愚昧阶段。 [ 原注:《盎格鲁撒克逊历史》(History。of the Anglo-Saxons)第二卷第五二五页。 ]
这场灾难性的约克战役过了一百五十年之后,达勒姆的西米恩写了一部书,证实了下面的悲惨景象:
侵略军到处袭击,使各地血水横流,哭声哀切。他们用火与剑毁灭了各处的教堂和修道院。他们每离开一个地方,身后留下的只是断壁残垣。其破坏程度如此之大,使我们今天很难发现这些地方的陈迹,也看不出它们往昔繁荣的任何迹象。 [ 原注:《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第二卷第五二四页。 ]
但是,伊瓦尔还要征服默西亚王国。谁都知道,在大约一百年的过程中,默西亚代表着英格兰的力量。伊瓦尔兵临诺丁汉城下,默西亚国王向西塞克斯王国求援。西塞克斯的老国王已经去世,他的两个儿子——埃塞尔烈德和阿尔弗烈德——答应出兵援助。他们派兵营救默西亚国王,建议同他一起向围城的敌人发动进攻。但是默西亚人退缩了,要同敌人举行和谈,伊瓦尔在斗争中软硬兼施,他没有损坏约克和里彭的教堂,他愿意在诺森伯利亚扶植埃格伯特为附庸国王,又在八六八年通过和谈协议确定了他在诺丁汉的宗主地位。然后,他就在约克过冬,加强自己的力量。
就在丹麦人实行着攻城略地的可怕计划,由东英吉利向外扩展,征服默西亚,洗劫诺森伯利亚的时候,西塞克斯国王和他的兄弟阿尔弗烈德在悄悄地加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他们和敌人势均力敌,但这种均势非常脆弱,并不可靠,那怕再多一丝一毫的压力,对他们也必然是致命的。所以,伊瓦尔在破坏诺丁汉协议和杀害东英吉利国王埃德蒙之后,突然永远撤离英格兰,这使他们如释重负。据北爱尔兰史料记载,北欧人的两个国王——奥拉夫和伊瓦尔——于八七〇年从苏格兰又来到都柏林,“许多撒克逊、布立吞和皮克特俘虏被带到了爱尔兰”。最后还有这样一条记载:“爱尔兰和不列颠境内所有北欧人的国王伊瓦尔于八七二年去世。”他曾经征服默西亚和东英吉利,攻占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的重要据点丹巴顿。他满载战利品,以不可一世的气概在都伯林定居下来,两年后在那里溘然长逝。虔诚的编年史家都说,他“长眠于基督的怀抱之中”。看来他生前万般显赫,死后又备享哀荣。
* * *
丹麦人每年在不列颠岛上的逗留时间越来越长了。每年夏季他们乘船前来,焚烧抢掠,但是每年也都愿意在这块气候宜人、草木蒇蕤的土地上到处闲游。最后,武士们感到离家劫掠的时间已久,而他们所征服的地方又比较安定,他们便把家眷迁来了。于是,在海盗的劫掠杀戮以后,拓居运动又一次开始了。丹麦人的拓居点和撒克逊人的拓居点有所不同,前者都是军营,其界线就是前线,有一系列据点作为它的后盾。斯坦福德,诺丁汉、林肯、德比和莱斯特是新入侵者的基地。在它们的边界线内,这十年的士兵必然是下十年的殖民者和地主。丹麦人在英格兰的殖民活动主要是军事性的,他们用剑开路,然后在当地获得牢靠的立足点。一开始,武士型的农民就要求得到与普通农民有所不同的社会地位。撒克逊人在这里已经住了四百年,有资格成为这里的主人,但是他们的民族没有统一组织起来,不能在他们居住的这块土地上打退来自海外的突然进攻,因此几乎完全屈服在丹麦侵略者的脚下。他们之所以没有完全屈服,是因为在那个混乱的衰落时代突然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历史上每一个危急关头几乎都能化险为夷,都是出于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