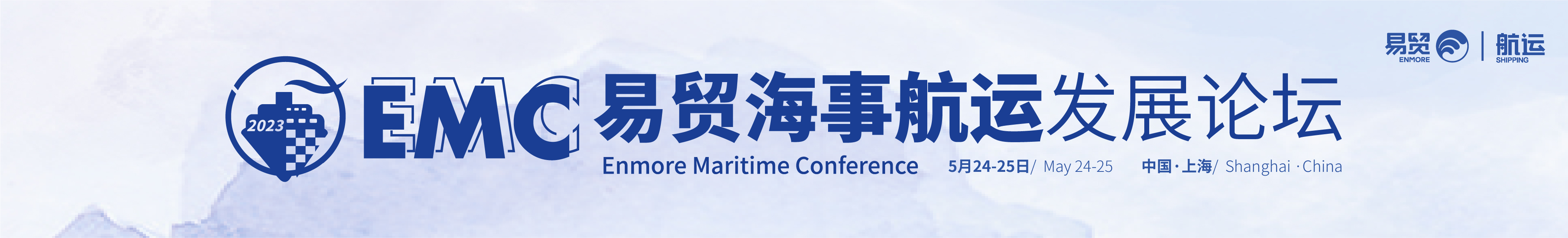江亚轮海难 史上死难人数最多的沉船惨案【史略】
江亚轮海难中,两千多条生命,永远消失。遇难人数之多,不仅在中国航运史上,即使在国际航运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在世界航海史上,泰坦尼克号也许是最著名的海难,却不是遇难人数最多的。泰坦尼克沉没夺去了1500多人的生命,而最大的一次海难,死难人数超过泰坦尼克的一半以上。
很不幸,这次惨痛的海难发生在六十多年前的中国。
1948年12月3日,江亚轮满载3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开往宁波,在经过吴淞口外约15公里的里铜沙洋面时,船体突然爆炸,尔后沉没。2300余人,在突如其来的惨案中罹难。
因为动荡的时局和国民党政府对事故的刻意隐瞒,江亚轮海难事故调查没有完成。随着年代日渐久远,江亚轮沉没的原因至今依然迷雾重重。有人说巨轮是被国民党飞机的炸弹炸毁,有人说是船身触到了水雷,甚至有人说江亚轮被炸是为了刺杀蒋经国……
今天,我们通过幸存者的回忆,重新拼凑起这场海难的诸多历史细节,重新走入那个让2300多个无辜的灵魂葬身海底的黑色夜晚。
最后的航程
1948年底,黄浦江上的上海外滩十六铺码头比往年更加嘈杂混乱。
战火临近,上海这座当时远东第一大城市人心惶惶。许多寓居上海的外乡人或因暂时失业,或为避开城市乱局,或是惦念乱世中的故乡,纷纷打算回乡。宁波是在上海谋生的外乡人最大来源地之一,当地还有冬至祭祖的风俗,因而从11月下旬开始,从上海到宁波的沪甬航线就格外忙碌和拥挤。
12月3日下午,江面平静,清风徐徐,冬日里难得的好天气。江亚轮停靠在十六铺码头边上,它是沪甬航线上最先进、豪华的一艘大型客货轮。
江亚轮原是日本东亚海运株式会社所有,原名“兴亚丸”。这艘船长102.4米,排水量3365.7吨,马力2500匹,航速18节,原设计可载客1186人。抗战胜利后,江亚轮被国民政府海军总司令部接收。国民政府为补偿国营招商局在抗战期间沉船封港的损失,旋将江亚轮等五艘轮船转拨招商局营运。经招商局改造后,该船可载旅客2250人,设有特等餐厅、休息室等,是上海招商局六大新型客轮之一。
到1948年时,江亚轮船龄未及10年,仍处“壮年”,无论外观、设备,在当时均堪称一流。停泊在繁华的上海滩,江亚轮也是黄浦江上繁忙船队中的明星。
等待上船的客人早已在码头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排在队伍第一个的叫严阿土。他是上海电池厂的一名普通宁波籍工人。因为买的是统舱(散客,最低等舱位)票,没有铺位号,所以他早早来到码头,希望能早上船占一个好位置。
临近开船,上海闵行南货店老板的女儿徐小文和她的未婚夫林瑞生才坐着人力车匆匆赶来,她要去宁波看望外公外婆。出门前收拾东西、梳妆打扮花了太多时间,险些迟到。
许多年后,徐小文和家人回忆登船的一刻,最深刻的印象是她挎着林瑞生的胳膊走过检票口,满心的紧张和幸福。
登船队伍的旁边,几个票贩子在兜售黑市票。宁波镇海人金国平一手拉着妻子,一手拉着才过一周岁的儿子,和票贩子讨价还价。
票贩子开价太高,他们夫妻决定第二天买着船票再走。金国平一只脚已经踏上了车夫的三轮车,一个票贩子却突然拉了他一把,压低了船票的报价。
金国平后来反复念叨,他作出了一个悔恨终生的决定。一家三口拿着两张三等舱的票,通过了检票口。
船马上就开了,登船的舷梯已经抬离了码头。在上海一家军服厂打杂的19岁青年邹信芳从码头上飞奔而来,手里挥着头一天买到的统舱票,大喊:还有乘客!
江亚轮不会为一个统舱乘客再放下登船梯。码头上的工人告诉他,船尾有小门,还在上货。邹信芳赶紧跑过去,找到一个搬行李的,塞给对方几张钞票,终于跟着行李夫穿过后门,踏上了江亚轮。
邹信芳大概是最后一个登上江亚轮的人。
根据现存于上海档案馆的当天江亚轮乘客名单统计,12月3日共售出船票2207张,加上江亚轮船员186人,那天在江亚轮上有案可查的人员为2393人。
实际人数却远不止于此,江亚轮上还有大量的“黄鱼客”。
所谓“黄鱼客”,指的是没有船票、通过各种关系登船的人。
江亚轮海难幸存者戴仁根就是一个“黄鱼客”。戴仁根回忆,那年他只有18岁,在上海一个商行当学徒。因为没有买到船票,他找到了在江亚轮上做水手的舅舅。舅舅把他带上了船,安置在二等舱。
宁波晚报编委蔡康是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因为家庭和工作的关系,他追访、研究江亚轮海难已有数十年。
蔡康告诉记者:“除了有据可查的乘客名单,还有后来在船上补票的400多人,军人和孩子不用买票,大约300人。在船员的庇护下躲过查票的据说有百余人,保守估计船上应该有3200余人。”
超载,对那个时代沪甬航线上的轮船来说司空见惯。江亚轮也这样航行过不知多少次,没有人觉得有何不妥,甚至很多人把超载当成了理所当然的牟利手段。
当天15时30分,江亚轮船长沈达才上了船。沈达才从1934年10月开始船长生涯,到1945年5月担任江亚轮船长的时候,已是阅历丰富的“老船长”了。
沈达才的孙子沈永清,在沈达才身边长大,却几乎从未听他谈起过江亚轮的事,问他也不愿回答。沈达才逝世后,沈永清撰写《江亚轮船长人生沉浮》怀念爷爷,也只能从档案记载和他人的回忆中来拼凑当时的海难事件。江亚轮是沈达才一生的隐痛。
而沈达才最后一次登上江亚轮时,原本要开启的是一次轻松的航程。当天的气象报告,晴到少云,气温3摄氏度-7摄氏度,风力2-3级。这是冬天里非常适合航行的好天气。
16时整,沈达才下达指令:开船。江亚轮拉响了长长的汽笛,离开了十六铺码头。
爆炸
江亚轮的最后一条航行记录是,18点35分,依照既定航道驶入吴淞口里铜沙浅滩附近海面。
这条既定航道是从十六铺码头起航,沿着黄浦江驶入长江,顺流而下进入大海,然后右转,沿着海岸到达宁波。航线距离不长,江亚轮用不了一夜就能跑到。里铜沙浅滩附近已经进入大海,通过了船只往来穿梭的吴淞口,下面的航程就轻松了。沈达才放心地离开驾驶舱,去餐厅吃饭。
冬天的夜来得很早,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
通过水手舅舅上船的戴仁根没有船票,虽然舅舅把他安置在二等舱,但那里并没有他的铺位,只能自己找地方待着。他无所事事地在船上闲逛,来到三等舱左前的船舷旁,眺望夜色中的大海。戴仁根记得,他看到江亚轮前方有一两处灯光,应该是有小船在航道上。江亚轮鸣响了两次汽笛,小船很快让开了。
就在汽笛声响过几分钟后,船体后部忽然传来炸雷般的一声巨响,江亚轮像打了个冷颤一样震颤了一下,正准备回到船舱的戴仁根被晃了个趔趄。
随后,江亚轮上所有的灯都熄灭了,顿时陷入一片漆黑。
沈永清说,沈达才是在离开驾驶舱大约10分钟后,突然听到“轰”的一声,同时感到船身猛烈地震动。他慌忙跑出了餐室,直冲驾驶舱。
江亚轮上已经乱作一团,上等舱的乘客们冲出舱室,不知所措地拥挤、冲撞着,到处都是哭喊、惊叫声。
沈达才赶到驾驶室,这里只有几个水手在值班,大副、二副或不在值班时间,或不在岗位上。爆炸骤然发生,沈达才一时搞不清究竟是什么爆炸,但可以肯定爆炸发生在船上,威力巨大,江亚轮很可能因此沉没。他依据着十几年的船长经验,几乎本能地向舵手下令,船头向右转90度,离开航道,紧急冲滩。
对沈达才的这个命令,蔡康分析说:“这是江亚轮发生爆炸后第一时间能做出的最正确的决策。沈达才显然很熟悉这条航道的水文地理,里铜沙浅滩一带水不深,让江亚轮冲滩是想在浅滩搁浅。虽然这样船体会受损,但如果冲滩成功,或许可以阻止船体的下沉。”
但是,在那个漆黑的冬夜,冲滩没有成功,汹涌的海水没有给江亚轮留出冲滩的时间。
沈达才下令冲滩后,没有得到更多的爆炸情况汇报,他只能自己去船尾查看。然而江亚轮的走廊、过道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乘客,沈达才艰难地推挤着众人前行了一段,最终决定放弃,又折回驾驶舱。
此时,几个高级船员和水手也来到了驾驶舱,带来了新的情况。轮机长和司炉报告说,轮机没有问题,锅炉也没有爆炸。这两处没有发生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江亚轮是自身爆炸。但无论是自爆还是外力造成爆炸,爆炸都已经发生,江亚轮面临的是灭顶之灾。
更坏的消息是,江亚轮的电报房在船后侧,爆炸中被彻底炸毁,报务员一死一伤。电报是当时在海上最快捷的通讯方式,江亚轮已经没有了这条呼救的途径。
另一种呼救的方式是汽笛。国际通行的轮船遇险呼救信号,是六声短汽笛。而江亚轮的汽笛仅仅短促地响了一声,就再也发不出声音,像是留在世界上最后的呜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