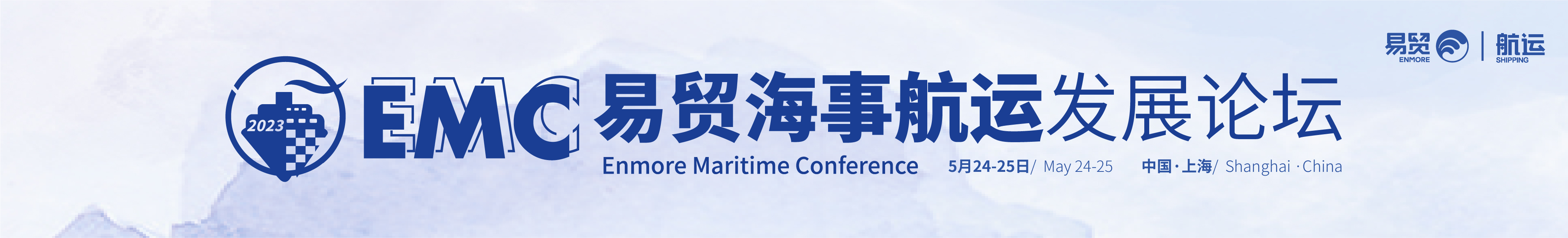大航海时代:明帝国兴衰的缩影【史略】

郑和宝船模型
在这些危机的打击下,明朝的统治者——不管他们情愿不情愿,都必须使国家退回到朱棣即位前的内向状态中去。成化十三年,1477年,是朝廷企图复苏郑和伟大航海事业的最后一次尝试,身兼东厂总管的宦官汪直,曾经索取郑和的航海日志,但兵部郎中刘大夏却焚毁了这一记录。
600年,作为明帝国首都的南京曾经亲眼目睹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从1405年到1433年,郑和庞大的宝船队七次从南京龙江关缓慢地驶入长江,借道太仓附近的浏河口进入波涛汹涌的东海,然而这些奠定了明帝国15世纪海上霸主地位的行动并没有使南京作为一个著名的海运城市而流传于世,仅仅在郑和最后一次泛舟下海后几十年,曾经宏伟的南京宝船厂就变成了荒芜河滩上的小作坊,宽阔的浏河入海口也逐渐淤塞。同样,当1498年达茄马带领他的小舰队到达东非时,当地的原住民对他们带来的诸如玻璃珠、粗呢等礼物不屑一顾,他们告诉欧洲人,在很久以前,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过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为何明帝国的海上事业在最辉煌的顶峰突然衰落?答案似乎必须从曾经作为它诞生地的遗址中才能找到。
宝船与奢侈的肮行
相对于整座喧闹的南京城,位于南京滨江路与草场门大街的宝船厂遗址还算是一个静谧的地方,尽管遗址的门口已经打出布告,宣告即将把这里变成拥有包括南洋半岛景观群落、波斯湾景观群落,乃至明式水乡与小吃街的“郑和下西洋文化公园”,但除了一些在建筑工地上繁忙的工人,几乎没有游客来参观这支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称为“600年前的中国无敌舰队”诞生的地方,茂密的荒草与新修建的石板步道环绕着三座“作塘”,布满藻类的水面使得它们看起来是已经淤塞的沟渠。然而许多史学研究者认为,这里,而非那座位于西北,已经荡然无存的明代龙江船厂,才是制造那些犹如海上移动城堡般“宝船”的确切地点。“我从1959年就住在这里,从三叉河口到现在的银城花园,漓江路。有两公里长的地方都叫宝船厂。”新华造船厂退休干部杨斌对记者说,“清代管中山路这一带叫宝船滩,这里的老百姓以南为上,北为下的原则,将这里称呼为上、中、下宝船,直到民国初年重新规划南京时更名为中保村、上保村、下保村”。
“作塘,其实就是制造宝船的干船坞,在解放初期还能看到6个作塘,但今天就只剩下3个。宝船厂当年就处于长江岸边的河漫滩地带,首先在作塘的位置挖淤加深形成塘口,把淤土堆积在作塘两侧,然后再从其他地方运来坚实的黄土,再次加固,经过夯打形成堤岸。”曾参与过2004年6号作塘发掘清理工作的江苏文史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祁海宁对记者说,“这里应当可以制造相当规模的船只,因为6号作塘长为400米,宽是40米。1957年就在这里发现高达11米的大型舵杆,我们还找到了34处起到承重作用的造船墩台和上千件造船工具和船板残件。”
考古发现是否能证明这些海上霸主确实存在,而非演义小说中的夸大杜撰?答案似乎是肯定的,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坚称,早在宋代,中国就拥有了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从而自阿拉伯人手中夺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贸易,“它们平均大约100英尺长,25英尺宽,载重量可达120吨。在设计上,船底变窄犹如刀锋一般,以便能够劈开海浪,从南部的福建以及浙江各路运来的松木,是造船的主要原料,船板相接的缝隙,是由丝绒碎布浸泡在桐油、石灰混合物之后再加以填补”。在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中,他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尔汗国时,乘坐的就是14艘四桅九帆的“福船”。而直到15世纪晚期才在欧洲出现的干船坞造船法也在沈括的《梦溪笔谈》中就有提及:“熙宁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
“从墩台和水深来看,宝船应为平底船。因为墩台地基到地表的落差只有4米左右,地基上还有大约1米高的台架,是工人攀登其上作业时所用,所以如果是尖底船,那么这个3米的吃水就肯定不够,所以宝船一定是平底船,其原型是明代的沙船。”江苏社科院研究员、南京郑和研究会成员季士家表示,“像福船这样的尖底船可以破浪,稳定性强,但吃水太深。平底船不但可以载运更多的货物,而且可以借助潮水停泊在沙滩上,作为陆地上的指挥办公场所。比如郑和第一次出使满喇加,就停留了相当长的时间,根据罗懋登《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的描述,最大号宝船的船体建筑包括头门、仪门、官厅、库司等建筑,无疑也证明了这一点”。
“成书于万历年间的《三宝太监下西洋通俗演义》中有许多真实的历史细节,不能当作一般的演义小说。”国家博物馆研究员王冠倬对记者说,“它证明了诸如曾经随同郑和出海的马欢、巩珍等人对宝船记载的确实性,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宝船完全可能存在过。宋徽宗时期为了出使高丽,造有6艘顾募客舟和神舟,客舟长十余丈,深三丈,阔两丈五尺,而神舟的尺寸甚至是客舟的三倍。在明代著名笔记小说《齐东野语》中,也记载了南宋时期洞庭湖杨幺起义军所用的车船,可以达到三十六丈的长度。”
在研究人员的讲述中,我们可以想到600年前在这片江岸上宛如好莱坞巨片一样的场景:来自江苏、江西、浙江、湖南、广东各省的能工巧匠,连同家属络绎不绝地来到明帝国的首都。在永乐初年的鼎盛时期,大约有2万~3万人在这里工作。他们按照技能被分为五厢:木作,铁作,舨作,篷作和索作,每厢大约一百户。另外还有更夫,搭罩篷作,以及照料搬运建材马匹的御马监匠役。在船厂中央,7座作塘中横亘着宝船巨大的龙骨,工人们在塘底先修筑以夯土为基础的墩台,在其上搭建名为“台架”的脚手架,然后在其上制造船身,先按照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然后再以层层叠加的木板构成船侧板,桅杆则竖立在已经丈量好,被称为“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子填塞船板间的缝隙,并覆以桐油和石灰等物,同样的涂料也被覆盖在联结船板的耙钉与马蹄钉上,以免铁锈腐蚀木头的纤维。桅杆使用的材料是坚固的杉木,而船身则使用榆木和来自四川的楠木。较大的船只拥有四层甲板,最底层用来安置泥土与石块等压舱物,第二层则是船员的宿舍与货舱,第三层甲板则连接舱外的厨房与舰桥,最高层的甲板往往是士兵们的作战平台。当船只完成后,作口的门闸就缓缓升起使得江水灌入作塘,从而让宝船直接进入浩荡的长江水道。四十四丈四尺的长度并非一个随便的数字,官方长度的一尺,从9.5到14英寸都有。地有四隅,中国位居“四海”之中,儒家思想中维系天下安定的品德,也正好有四种——礼、义、廉、耻。在整个船队中,除了最大的宝船,还包括载运供品的八桅马船,承载给养的七桅粮船,和使团成员乘坐的客船。根据马欢《瀛涯胜览》与《郑和家谱》中的记载,全体人员包括品级不同的太监,户部与鸿胪寺官员,乃至医生,军士,通事,书算手,买办,共计26000~27000人。
船队一旦开航,最为繁忙的恐怕就是那些“谙习水性,不畏风浪”的水手,他们用“牵星术”在黑夜的茫茫大海中准确判断船队的方位。“夫乘舟而惑者,不知东西,见斗极则痦也”。这种以观测星辰的海平高度来确定船舶纬度位置的方法早在《淮南子·齐俗训》中就有记载。在《武备志》中保存的二十页郑和海图中,就拥有四幅“过洋牵星图”,海员们所用的观测仪器,称为“牵星板”。明代笔记小说家李诩曾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描述过这种仪器,是12块边长2至24厘米,带有刻度的乌木板。观测者手持牵星板,使板面与海平面垂直,下边缘与海天交界线垂直,上边缘与所测天体相接,板上引一长绳以固定牵星板与观测者眼睛之间的距离,计算单位为“指”与“角”,一指大约是今天的1.9°,折合四角。在《郑和航海图》中,记载的星名达到18个之多,包括被称为“北辰”的北极星,以及“灯笼骨星”的南十字座。如果云雾遮蔽了这些天上的导航者,郑和的水手们就会转而借助水罗盘来调整航向,根据现存于牛津大学鲍德林图书馆《顺风相送》与《指南正法》两部罗盘针经,我们可以知道在成圆形的罗盘上刻有八个天干,12个地支和4个卦位组成的24针位,每个针位之间相隔15°,能够方便地实现四十八方向的导航。负责这些复杂观测职务的海员被称为“火长”。这些经验丰富的首领海员还要同时担负起计算时间与航速的责任,在海船上,一昼夜被分为十更,每更大约是2小时24分钟,良好天气条件下,宝船船队的航行速度,大约是一更20英里,即每小时八节。这个速度无疑是这些大小不一的船只都能轻松保持的,尽管如此,许多专家学者仍然认为船队在海上航行时不可能保持《武备志》中复杂的密集队形,而很可能是简单的一字长蛇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