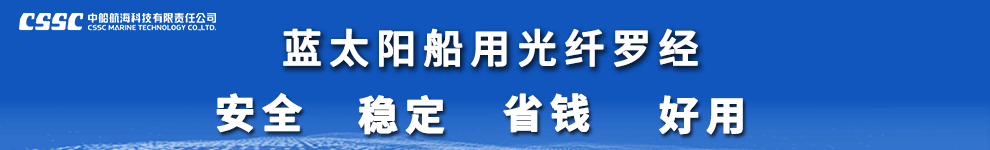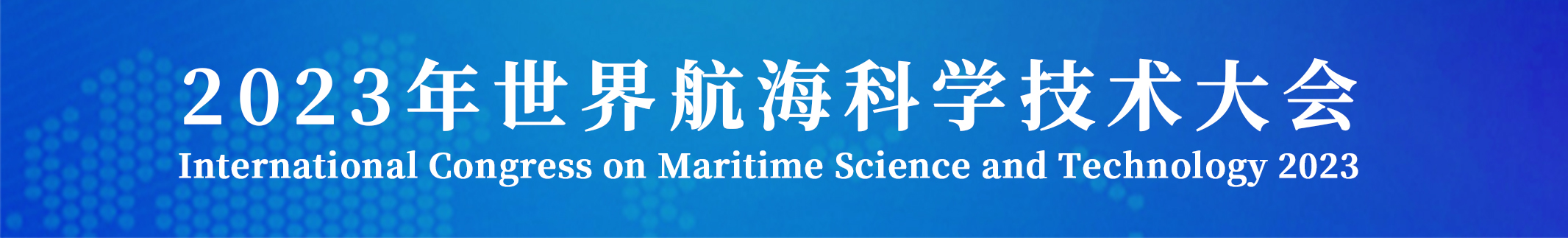司玉琢:商船与军舰碰撞的法律适用

《海商法专论(第三版)》第256-260页
一直以来,商船与军事舰艇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的碰撞时有发生。碰撞发生后,应如何适用法律,是一个复杂而又现实的问题。[1]在我国《海商法》下,情况亦是如此。
商船与军舰之碰撞涉及的法律问题主要是对《海商法》第1条、第3条和第八章、第十一章的适用问题。其中两个关键问题需要进行解释:一是根据《海商法》第1条和第3条之规定,能否得出结论,与军舰发生的任何法律关系均不适用于《海商法》各章?二是商船所有人是否可以享受中国《海商法》下的责任限制?
一、商船与军舰的碰撞责任不适用《海商法》第八章规定
船舶碰撞引起的海事请求,其损害赔偿基本原则所适用的法律,首先应考虑我国《海商法》是否适用。《海商法》第165条规定:“船舶碰撞,是指船舶在海上或者与海相通的可航水域发生接触造成损害的事故。前款所称船舶,包括与本法第三条所指船舶碰撞的任何其他非用于军事的或者政府公务的船艇。”[2]本条第2款对碰撞当事船舶的限定是:碰撞的一方为本法第3条规定的船舶,即“本法所称船舶,是指海船和其他海上移动式装置,但是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和20总吨以下的小型船艇除外”;另一方为“任何其他非用于军事的或者政府公务的船艇”。这就是说,军舰和商船之间的碰撞并不符合《海商法》中船舶碰撞定义中的主体要件,因此,碰撞双方有任何一方是用于军事的或者政府公务的船艇,都不适用我国《海商法》第八章的规定,而应适用一般侵权行为法之规定。
我国《民法通则》第121条规定,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第117条规定,损坏国家的、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并应当赔偿损失。第119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根据《民法通则》的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在军舰与商船的碰撞责任适用:
第一,过错责任原则。侵权造成的人身、财产损害原则上实行过错原则,除非法律另有规定。《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这是公平原则的规定,适用这一条款的条件是碰撞双方都无过错,这在船舶碰撞中是少有的。
第二,实际赔偿原则。侵权造成的国家的、集体的或个人的财产损害,实行实际赔偿原则,除非特别法另有规定。《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侵权人的责任限制问题,而且这一原则与财产的所有制性质没有关系。
但是,商船与军舰的碰撞责任不适用《海商法》第八章,并不意味着与军舰有关的碰撞责任的过失认定、责任划分和责任限制都不适用《海商法》的规定。
二、商船与军舰发生的所有法律关系并非均不适用《海商法》
商船与军舰可能产生多种法律关系:人身伤亡、财产损害的侵权法律关系;船舶优先权法律关系;海事赔偿责任限制法律关系;海难救助法律关系等。判断某部法律是否适用一个具体的法律关系,既要看该法律的适用范围或调整范围,又要看调整该法律关系的具体规定。《海商法》第1条规定:“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制定本法。”根据本条规定,显而易见,军舰和商船之间发生的碰撞侵权不属于海上运输关系,但是否属于海上船舶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因为《海商法》在总则部分第3条明确规定了用于军事的、政府公务的船舶被排除在《海商法》的船舶定义之外,所以,军舰与他船发生的法律关系不能被纳入海上船舶关系的范畴,从而就排除了整个《海商法》对其的适用。
笔者认为,《海商法》条文区分“总则与分则”,这是一种基本的立法技术。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下面的观点可以说是共识性的:“分则规定可以弥补总则规定的法则或法命题”,以及“分则规定可以部分或全部修正总则规定”,而且“当分则规定部分或全部修正总则规定时,就在修正范围内排斥了总则的适用。在此情形下,分则规定与总则规定具有特别法与普通法的关系,适用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3]因此,在决定某一社会关系是否适用某部法律的规定时,必须具体考察分则中不同章节的具体规定。《海商法》调整着各种各样的特定社会关系,每一章针对不同的社会关系都有其独立的适用条件,根据《海商法》第3条的规定,笼统地讲《海商法》在整体上是否适用,其实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的。军舰对《海商法》的适用问题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海商法》每一章的规定是否变更了总则的一般性规定。
例如:军舰损害同样可以作为船舶优先权的债权项目向肇事船舶主张船舶优先权(第二章第22条);《海商法》第九章第192条同样适用军事舰艇救助海上财产,可以获得救助报酬。此外,《海商法》中的拖航一章,保险一章,船员一章,责任限制中的港口设施、灯塔、灯标损坏本身都不是《海商法》第一章第1条所规定的“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但是它们和船舶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关系都属于和船舶有关的主体之间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分属《海商法》的不同章节,作出适用相应章节的具体规定。
三、商船与军舰碰撞,商船适用《海商法》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
1.法律解释
军舰方向商船方提出的侵权索赔,商船应有权援引《海商法》有关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规定。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其理由如下:
第一,从文义解释上看,《海商法》在总则第3条将军事的、政府公务用船排除在“船舶”的概念之外;在第204条又规定,“船舶所有人、救助人,对本法第二百零七条所列海事赔偿请求,可以依照本章规定限制赔偿责任”。结合该两条,将《海商法》第3条船舶的定义纳入第204条的规定,进行字面上的理解就是:军舰所有人不能享受责任限制权利,而商船所有人可以享受责任限制。因此,在军舰和商船碰撞中所产生的责任限制问题就有适用《海商法》的余地。
第二,从比较法解释来看,有的国家的立法例可以佐证这一点。例如《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1999年4月22日联邦议会通过)第3条第2款规定:“除本法直接具体规定的情形外,本法典不适用于:军舰、海军辅助设施和其他国家所有或经营的和仅用于政府非商业服务的船舶;国家所有的非商业货物。在本法典直接规定的情况下,本法典规定适用于本款所列的船舶和货物,但该规定不能作为捕获、扣押或拘留此类船舶和货物的依据。”[4]
《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的规定表明了虽然将军舰排除在船舶的定义之外,但是,该规定并没有排除该法律具体各章涉及与军舰有关的法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我国《海商法》第3条的除外规定,没有像《俄罗斯联邦商船航运法典》规定的那样严谨,但从立法本意考察,并非将所有与军舰发生的所有法律关系排除在外,只是出于保护国家利益的需要,赋予军舰在捕获、扣押或执行方面的特权,这在各国都是一致的。
第三,从扩张解释来看,其系指法律条文之文义失之过窄,不足以表示立法真意,乃扩张法律条文之文义,以求正确阐释法律意义内容之一种解释方法。[5]它和目的性扩张是不同的,前者属于法律解释方法之一种,而目的性扩张则是法律漏洞的补充方法。[6]《海商法》第1条之规定,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海上运输关系和船舶关系”,文义失之过狭,无法表示立法真意。故应对其作扩张解释,即使军舰不符合《海商法》第3条定义之船舶,但与军舰发生的法律关系仍在《海商法》第1条文义“射程”范围内,应属于《海商法》第1条之调整范畴,有其适用之余地。
第四,从历史解释来看,它通过对立法过程中资料、背景、记录和文件进行参酌。“主要在探求,某一个法律概念是如何发生,如何被接受到法条中来;某一条文、规定、制度是如何被接受到法秩序(die Rechtsordnung)中来;立法者是基于哪些价值决定去制定它们,以帮助了解法律意旨之所在。”[7]我国《海商法》船舶碰撞一章是参考《1910年碰撞公约》起草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七届二十八次会议通过《海商法》后不久,我国就参加了该公约。[8]该公约第10条规定,“在不影响以后可能缔结的任何公约的情况下,本公约的规定不以任何方式影响各国现行有关限制船舶所有人责任的法律”。这就是说,责任限制法律制度是独立于船舶碰撞法律制度、且优先适用的(参见第十一章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专题研讨“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优先适用原则”)。军舰与商船碰撞不适用《海商法》第八章之规定,并不影响商船所有人责任限制适用《海商法》第十一章之规定。
第五,从目的解释上看,“在任何法律规范后面都隐藏着服从特定目的与目标的、立法者的、法政策学的形成意志”。[9]目的解释是指以法律规范目的为依据,阐释法律疑义的一种解释方法。在作目的解释时,不可局限于法律之整体目的,应包括个别规定、个别制度之规范目的。我国《海商法》第十一章规定的责任限制和《1976年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公约》是一致的。二者之所以规定与民法损害赔偿制度相悖的特殊赔偿制度,将责任人的赔偿责任限制在一定范围内,其立法旨意在于保护航运中的船舶所有人,促进海运业的发展。[10]因此,在解释《海商法》第十一章时,应该注意到该个别制度之规范目的。此外,《海商法》第207条第1项规定的“对港口工程、港池、航道和助航设施造成的损坏”的限制性债权,多数情况下,属于国家财产的损失,同军舰损害的性质是类似的。根据《海商法》的规定,并没有因为港口设施损害性质的特殊和不是《海商法》第3条所适用的船舶而使其不适用《海商法》第十一章责任限制的规定。同样,也不能因为军舰的特殊法律地位和不是《海商法》第3条所适用的船舶而改变商船责任限制的立法宗旨。因此,不管碰撞的对方是谁,给予商船责任限制是符合我国《海商法》第十一章的立法目的的。
第六,从体系解释上看,体系解释乃指“以法律条文在法律体系上之地位,即依其编、章、节、条、项、款之前后关联位置,或相关法条之法意,阐明规范意旨之解释方法”。[11]它的作用在于消除法条之间的互相矛盾和体系违反。第十一章的立法意旨在于给予船舶所有人的责任限制利益,而不管该限制债权的相对方是谁;而《海商法》第3条将军舰排除在海商法的调整之外,从表面上看,《海商法》第3条之规定和第十一章的规定似乎存在着矛盾。但是,根据该不同规定在海商法中所处的位置进行体系解释,这种矛盾是可以消除的。第3条位于《海商法》第一章总则部分,而第十一章责任限制的规定是在分则部分。如上文所述,《海商法》的总则部分为一般概括性规定,而分则部分是针对特别法律情形之特别规定。更重要的是,《海商法》第3条是从法律关系客体的角度进行规定的,而第204条是从法律关系主体的角度去规定的,所以,两者是互相补充的,根本不会产生矛盾。[12]结合两者,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商船和军舰之间发生的侵权行为而导致的赔偿责任,商船所有人适用于责任限制规定,而军舰所有人则不适用于责任限制的规定。这样,体系解释得出的结论和目的解释是一致的,完全符合《海商法》第十一章的立法本意。
2.司法判例
1960年加拿大最高法院在TheQueen一案中,作出终审判决。案件涉及皇室所有的活动式浮桥被船舶W. E. Fitzgerald号碰撞致损。一审法院判决全部由被告船舶所有人承担责任,但是可以享受责任限制。被告不服,上诉到加拿大最高法院,加拿大最高法院只更改了责任比例,判定双方互有过失,而对于责任限制,仍然认同了一审法院的判决,赋予被告责任限制的权利。[13]
最为类似的案例是1999年美国海军军舰Radford号和沙特阿拉伯商船Riyadh号碰撞案(USSArthur W. Radford),该案涉及双方互有过失的碰撞责任问题,法院判决沙特商船有权享受责任限制。[14]
3.立法例
在1916年以前,囿于严格的主权豁免原则,美国对有关与军舰发生侵害的法律关系一律实行豁免的政策,但是随着军舰和商船侵权案例的增多,美国在1920制定了《海事诉讼法》(theSuits in Admiralty Act,简称SAA),规定禁止对国有船舶进行扣押。除此之外,如果国有船舶从事的行为是商事行为,其造成的损害不具有豁免权,但是,该法并没有解决国有船舶从事公务行为所造成的损害问题。[15]尤为惊人的是,从1922年到1925年间,美国共发生了450起国有船舶和商船相撞的事故。于是,美国在1925年制定了《公务船舶法》(PublicVessels Act,简称PVA),目的是使公务船所有人(国家)和商船所有人一样承担海事法下的责任。[16]由于在很多情况下难以区分国有船舶是从事商业活动还是公务活动,美国于1960年删除了《海事诉讼法》中“作为商船受雇于国家”(employedas a merchant vessel)的规定,显示了进一步减弱对公务船进行特殊保护的迹象。所以,从比较法的角度观之,给予商船方责任限制的权利是合乎情理的,否则的话,很难解释为什么同一商船因为碰撞对象的不同而要承担截然不同的责任。
我国《海商法》第十一章作为《民法通则》的特别法规定,恰恰是在《民法通则》没有规定或与《民法通则》规定不一致时才起作用。责任限制是对民法实际赔偿责任的一种例外规定,属于特别法的范畴。在不违背《民法通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根据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海商法》第十一章具有优先适用的地位。同理,假如我国将来规定了军舰的特殊赔偿责任制度的《国家补偿法》,那么,军舰对商船的碰撞赔偿责任将是按照调整军舰赔偿责任的特别法——《国家补偿法》,而不是依据《民法通则》进行确定,这也是符合法律合宪性要求的。
四、小结
一部法律制定出来,只不过对某种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只是纸上的法律。而将纸上的法律具化成现实的法律则是通过法律解释进行的。法律解释是法律文本和解释者两方面的视阈融合(fusion of horizon)的过程。一方面,解释者需要通过各种手段去恢复原来历史的原本视阈,这包括历史解释、文义解释等等;另一方面,解释者又要根据自己的视阈——特别是经过甄别后的合法先见——与历史视阈达成一种持续性的转换。从而解释者不断地扩大并修正自己原有的视阈,其结果会形成一种新的、更大的视阈,而这种视阈又会成为更新、更大一轮理解的出发点。[17]在法律解释中,不仅要注意到法律文本的含义本身,更要注意到法律文本所欲达到的目的,从而更好、更准确地去理解、解释和应用法律。
[1]SeeDavidR.Owen,TheOriginsandDevelopmentofMarineCollisionLaw,51Tul.L.Rev.759(1977).
[2]《1910年碰撞公约》第1条、第11条也有类似规定。
[3]易军、宁红丽:《合同法分则制度研究》,17~24页,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4]韩立新、王秀芬编译:《各国(地区)海商法汇编(中英文对照)》,下卷,1363页,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
[5]参见梁慧星:《民法解释学》,222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6]目的性扩张是指为贯彻法律规范意旨,将本不为该法律条文的文义所涵盖的案型,包括于该法律条文涵盖之案型种类之内。
[7]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276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8]中国《海商法》于1992年11月7日通过;1993年3月全国人大八届六次会议通过中国加入《1910年碰撞公约》;1993年7月1日《海商法》生效。
[9][德]伯恩·魏德士:《法理学》,319页,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10]参见吴焕宁主编:《海商法学》,347页,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
[11]杨仁寿:《法学方法论》,140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各国法律章节编排稍有不同,我国《立法法》第54条第1款规定:“法律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编、章、节、条、款、项、目。”
[12]笔者认为很多人之所以会觉得《海商法》第3条和第204条的规定矛盾,是因为根深蒂固地将“船舶”拟人化的结果,船舶在《海商法》里往往成了法律关系的主体,而不是客体。
[13]SeeGartlandSteamshipCompanyandLablancev.TheQueen,CanadaSupremeCourt,[1960]1Lloyd‘sRep.388.
[14]SeeIn reNat’lShippingCo. ofSaudi Arabia,147F. Supp. 2d 425,440~446(E.D.Va.2000).
[15]SeeClaytonG.Ramsey&VivienneMonachino,AdmiraltyClaimsagainsttheUnitedStates,5Mar.Law31,33(1980).
[16]Allenv.UnitedStates,338F.2d160,162(9thCir.1964),cert.denied,380 U.S. 961(1965).
[17]参见何卫平:《通向解释学辩证法之途》,201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来源:司玉琢 海商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