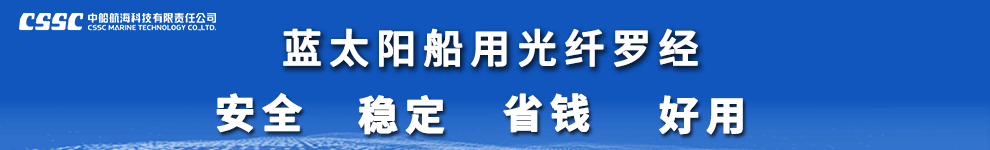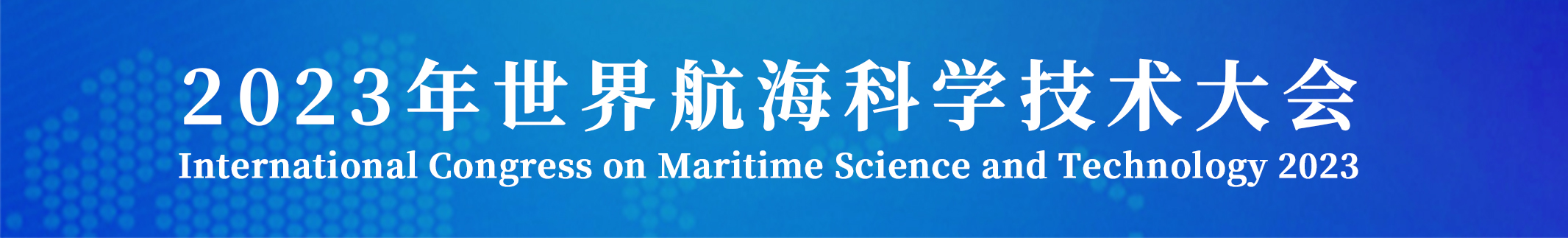四十三年前,珠江上沉船的那个夜晚
1972年,我高中毕业,进工厂做学徒,后来到广州市橡胶工业局当个小职员,当时叫“以工代干”。
1975年8月3日晚,轮到我值班,在局里过夜。那是盛夏,但局机关在一个小山包上,凉风习习,挺舒服,我睡得挺好。快天亮的时候,电话响了,是市委打来的,说两艘客船在顺德容奇蛇头湾沉没,上面有几百橡胶七厂的职工。我赶快报告局领导。
8月4日早上,我们已经知道大致情况。肇庆七星岩和鼎湖山是省里最有名的风景区。但当时从广州坐车到那里走的是很颠簸的黄沙公路,还得过两三个渡口,用船把车运到对岸。单程要四五个钟头,又累又麻烦。所以很多人愿意坐船,傍晚从广州出发,在船上睡一晚,第二天早上到肇庆;玩一个白天,黄昏上船,天亮就回到广州。
橡胶七厂是国营的,有四百多职工,搞汽车轮胎翻新,在工业大道。七厂的工会和团委组织职工到肇庆,可以带家属,有三百多人去了。他们在2日傍晚坐船出发,3日晚原路返回,刚过十二点就出了事。
8月4日下午,第一批幸存者回到广州。我跟着局领导坐机关里唯一的北京牌越野车赶去广州宾馆。那宾馆在海珠广场,当时是全市最高级的旅店。省领导设法避免社会不安,派船到出事的地方,把幸存的旅客分头送回广州和肇庆。因为有不少人听到传闻,在天字码头等待,回广州的旅客转到一个军用码头上岸,坐车到广州宾馆,先洗澡、换上干净的衣服再回家。我们在宾馆的大堂和走廊,看到很多穿同样天蓝色短袖衬衫的男女,都是刚从容奇回来的旅客。
在房间里,有些工友的头发、脸上和衣服还沾满棕黑色的柴油。那天凌晨,他们的红星245号客轮在蛇头湾跟红星240号客轮相对而过。每艘船有四百多乘客。红星245号上多数是橡胶七厂的职工。另一艘船上有团省委三十多人的参观团,去看肇庆的马安煤矿,那是“工业学大庆”的先进单位。月光明亮,江面平静。两艘船上多数乘客都睡了。
突然,开往广州的船转头向开往肇庆的船猛冲过去。那艘船连忙躲避,但已经来不及。开往广州的是一艘钢板船,而开往肇庆的是一艘用水泥做外壳的船。中国的水泥船是“大跃进”的时候开始发展的,原因是要大大增加航运力量,又缺钢材。但水泥船当客轮很不安全,那是明摆的。红星245一撞,红星240的水泥壳就破了个大口,红星245的船头深深插进去。两艘船成了个丁字。
两边的船员赶快商量,决定让横在江上的红星245号向前开,把水泥船推到岸边搁浅,使大家能够逃生。水泥船很重,钢壳船推了一会没推动,上面的驾驶员就开倒车,想保住自己的船。谁知钢壳船一后退,水泥船上的破口就失去了堵塞,江水轰地冲进去。水泥船马上下沉,船壳上的钢筋网钩住钢板船头的东西,使它没法完全退出。几分钟之内,两艘船一起沉到水底。水泥船的柴油从破口涌出,铺满江面。
二
两船相撞的时候,旅客们醒了,有些人摔到床下,头破血流。
因为船员们决定把船推到岸边,为了避免混乱,两艘船都打开广播,反复要求旅客留在自己的铺位。多数旅客服从管理,只有少数人到甲板上张望。红星245的驾驶员违反约定,两艘船突然下沉,甲板上的乘客急忙跳水。船舱里的人拼命往外冲,但走廊和楼梯很窄,窗户又装了铁条,很多乘客被绝望地困住。
这场灾难的正式名称是“八·四海事”。“海事”是专业术语,选这个词应该是小心避免对社会的刺激。
在广州宾馆,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走,打听情况,安慰工友。
局里成立“八·四海事善后办公室”,领导指定我做办公室主任,不是“善后办公室”的主任,那是局领导当的,是“善后办公室”里办公室的小头目,管秘书和后勤的事。我还不满二十,刚从学徒升为一级工。跟我一起干的同事资历比我深,经验也比我多。因为当时流行重用和培养青年的风气,所以有这不妥当的决定。
遇难者的尸体很快就运到广州殡仪馆。我和几个同事住到路对面的空军招待所,橡胶七厂的干部也住了进来,组织遇难者的亲属认尸。我们楼前天天停一辆民用牌的黑色奔驰轿车,应该是市领导在坐镇指挥。
最后统计死难者共432人,其中广州380人,肇庆52人。这是1949年以后中国最严重的航运事故。橡胶七厂遇难108人,包括职工75人,家属33人。殡仪馆缺乏冷冻设备,就是在几个大屋子里放些冰块,地板铺一层稻草,把尸体搁在上面。天气太热,冰很快融化,满地都是水。在江里打捞上来的尸体一下就肿胀变形,难以辨认。屋里又脏又臭,认尸辛苦极了。
那年头有不少非常糟糕的事,但普通百姓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时候是挺好的。本来认尸是亲属的事,但死者的亲人受到了太大打击。有些失去儿女的父母连自己都不知怎么生活下去,很难在恶劣的环境里辨认面目全非的尸体。于是同事和朋友尽力帮助。他们天天到殡仪馆来,做着世界上最难做的事。
三
这样的热心人很多,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局宣传队的工友。当时橡胶局挑二三十个青年工人,搞了一支文艺宣传队,住在市郊沙贝岛。那地方现在叫金沙洲,原来是个特供农场,为省政府养鸡、鸭、蛇和鹌鹑之类东西。1966年以后批判领导搞特殊化,农场关掉。橡胶局在那里建了橡胶六厂。局宣传队的人集中在这个厂排练,到各厂演出。生产企业养个文艺宣传队,当然不正常。但当时就是不正常的年代。无论如何,这不是那些年轻人的错。
宣传队里有两个七厂的工人,叫大家一起到肇庆玩,有八个宣传队员响应。8月4日凌晨撞船,橡胶机械厂工人、小提琴手陈少霏被震醒,不久发现船在下沉,觉得这是生死时刻。刚好他床头的窗户少了一根铁条,少霏赶快叫身边的舞蹈队员陈穗明爬出去。缺口很窄,穗明又背了个小包,卡在那里。少霏拼命推,穗明终于逃到外面。这时江水已经淹过窗口,少霏硬钻出来。船已经沉得挺深,他蹬腿浮到江面,大口喘气。太悬了,距离死亡可能只有几秒!船在江心相撞,两边离岸有三四百米。少霏在黑暗里看到陆地和山岭的轮廓,使劲游,最后气喘吁吁地到了江岸。
八个队友去旅游,只有少霏和穗明生还。宣传队的年轻人伤心极了,马上挨家看望去世朋友的父母,每天到殡仪馆寻找遭遇不幸的朋友。少霏也去了。那场灾难的刺激太大,他天天睡不着,昏昏沉沉,到了遇难队友家也不会讲话。但他觉得那是自己对朋友的责任,自己到了那里,就是对朋友家人的支持。
舞蹈队员姚衍仪的姐姐认定了妹妹的遗体,姚妈妈拿出女儿最好的衣服给她换上。宣传队员们一起参加葬礼。但容奇事故现场的军人在一具年轻女尸上找到工作证,确定那才是姚衍仪。宣传队的年轻人陪衍仪一家举行了第二次葬礼。在最悲痛的日子里,这样的陪伴不知有多重要。
那些年轻人把去世队友家里的遗物照下来,还做了张他们六个人头像排在一起的相片,作为纪念。局里的一个中层领导很不满意,说那些多情的青年表现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其实阶级是人的社会地位。波普尔说得好,一个人以什么为业,就属于什么阶级,不管原来干过什么。那位中层领导是工人劳动模范出身,但已经成为正儿八经的管理者,所以是管理阶级。而那些年轻人尽管过去是学生,当了工人就是工人阶级。同一个阶级的人也会有不同的情感和想法。在那个年头,小资产阶级是挺不好的身份。因为人家念过高中,感情细腻,就给人扣上异类的帽子,那很不宽容。
因为防腐条件太差,尸体在殡仪馆放了一个星期,就不得不全部火化了。容奇那边的尸体更没法保留,只能在当地掩埋。好些遇难者的家庭没有找到亲人的遗骸。
我们离开空军招待所,搬到工业大道口的橡胶工业研究所,继续做其他善后的事。
四
出事之前不久,橡胶局开“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各厂找了一些人来帮忙,其中有七厂的打字员谢妮。那是个小巧活泼的女孩。她的愉快很能感染人,大家都喜欢她。会议开完,到局里帮忙的人准备回工厂,在我们的办公室搞了个欢送会,大家坐下喝点茶,吃几块硬糖,讲些祝福的话。我跟谢妮开了几个玩笑。几天之后,我在橡胶研究所给谢妮填死亡登记表,心里真难过。
有人说,产业工人之所以伟大,一个原因是纪律性强。这是读书人的想象。一个七厂的年轻人拖拖拉拉,到大沙头码头的时候船已经开了。他从头上摘下草帽,扔给甲板上的朋友,说:“带着我的帽子去转一圈吧!”结果那家伙逃过一劫。命运无常,一至于此。
我们每天接待遇难工友的亲属。省政府为了安定人心,允许非直系亲属顶替,还把入厂的最低年龄降到十六岁。十六岁当工人,现在看当然不合适,但当时进国营工厂几乎是全国百姓的梦想。另外买了全票的遇难者有一千五百元的赔偿,买了半票的有七百五十元,无票儿童赔三百五十元。国营大厂工人每个月才拿四十多块钱,那赔偿是挺大一笔数。由于这些原因,善后工作总的来说还顺利。但我们仍然经常挨骂。他们失去了亲人,心情不好,可以理解。我们一直非常耐心。
过了十天左右,在橡胶研究所的工作干得差不多了。我和橡胶局五六个同事去七厂处理最后的事。四百来人的工厂,一下少了七十五个职工,这是巨大的损失。但七厂很快就恢复了生产。厂里多数都是事故的幸存者,刚刚逃出沉船的灾难。他们几天之内就稳定了心绪,大家默默分担去世工友留下的事情。
红星245和红星240在江中沉没,有个青年工人拼命游到岸边的甘蔗田,把照相机交给女朋友,又下水救人,结果再也没有回来。当地的村民听到动静,就敲响铜锣,一起赶到江边,推出舢板救人。村里的“赤脚医生”在岸上给捞上来的乘客做人工呼吸。后来那些农民一直照顾着两艘客轮的生还者,直到政府派船接走他们。
我们在橡胶七厂大概干了一个星期。
在法院,红星245号客轮的驾驶员说,跟水泥船相遇时突然转舵,是为了避开一艘无灯的小艇。但调查找不到任何证据。由于事故严重,他受到交通肇事的最高惩罚,被判七年徒刑。随后,珠江内河的客轮全部拆掉窗户上的铁条,水泥外壳的船只也被逐渐淘汰。
来源:大家作者:袁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