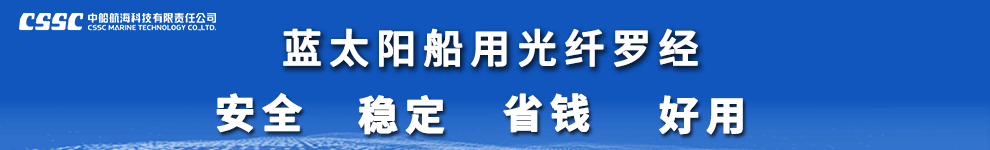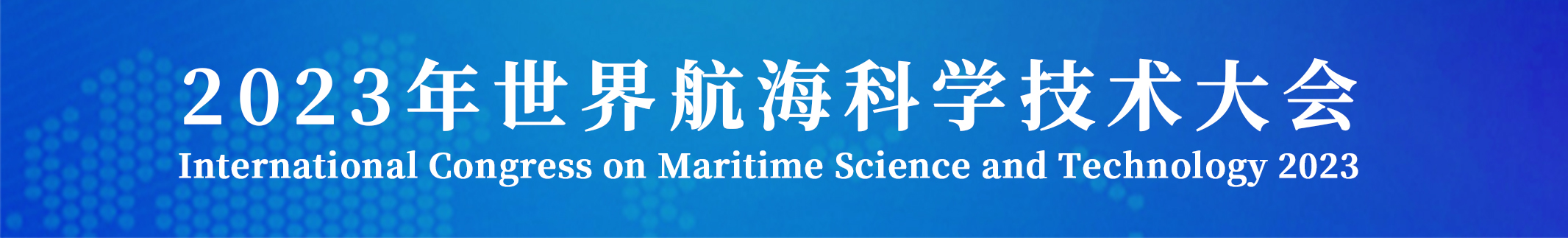船舶行业第一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黄旭华的“沉浮”人生

人物小传:黄旭华,核潜艇总体设计研究专家。祖籍广东揭阳,1926年生于广东汕尾,1949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造船专业。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中国船舶集团所属第七一九所名誉所长、研究员。1958年起一直致力于我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与发展,是研制我国核潜艇的先驱者之一,为我国核潜艇的从无到有、跨越发展探索赶超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研制核潜艇倾尽了黄旭华的一生,他也像这个潜在海底的国之重器一样,在生命的黄金阶段“沉”于深处,但他的人生与机械、图纸、数字描述的世界相比要宽广、丰富得多。他酷爱音乐,小提琴拉得不错,吹得一嘴好口琴,指挥过大合唱;有表演才华,能演话剧、歌剧。当然,还有因难以尽孝,亏欠亲人的无言真情。
接受记者采访当天,他围着一条款式陈旧、略显粗糙的黑围巾。这是他母亲留下的遗物,每到冬天,他总会围上它,虽然比这好的围巾家里有好几条。他说,要和母亲的气息在一起。
他中等身材,白发苍苍,已过鲐背之年,却精神矍铄。一只耳朵虽听不太清,谈起核潜艇却彷佛有了十二分精神。近些年,“浮”到台前,他获得鲜花掌声无数。有人问他,与隐姓埋名做科研时比较,更喜欢哪一种状态?他毫不犹豫选择“沉”的生活。
“闷着搞科研是苦,可一旦有突破,其乐无穷。”他斩钉截铁地回答。随后他微微一笑,像是在回味那些悠远难忘的岁月。熟悉黄旭华的人知道,这不是事后高调的大话。

黄旭华在办公室内(2016年12月20日摄)。新华社记者 熊琦 摄
(1)不变的痴气
在妻子李世英看来,黄旭华从始至终都是一身痴气的大男孩,“甚至有时候有点傻。”或许是“槽点”的实在太多,这位贤内助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
嫌理发店排队浪费时间,他让李世英给自己剪了几十年的头发。有时,李世英想以“罢工”的方式,逼迫他去理发店,却最终拗不过他对越留越长头发的熟视无睹。他不懂得料理自己,一次走去上班的路上,他感觉脚硌得疼,直到办公室,才发现是鞋子穿反了,脚上还勒出好几道伤痕。
他自己没买过一双袜子,对厨房里的事一窍不通。看着夫人忙,心里过意不去,想着帮助家里做点什么。买菜,他有个高招:到菜场,不挑菜,先找人,找看上去和李世英一样精通家务的人,人家买什么,他就跟着买什么。别说,这一笨方法还不赖。这是他自夸懂生活的得意之作。
有一次出差,难得有闲暇逛街,他依葫芦画瓢,跟在很会挑布的人后面,买了一块花布料。他颇为得意,也十分开心,心想用它给夫人做一件衣服,准好。当他兴致匆匆跑到夫人面前,准备邀功时,没想弄巧成拙。原来,李世英穿这种花布衣服好几年了。妻子理解他的痴气:他能熟练背出工程上的许多数据,就是不记得身边人穿了几年的印花衣服。
李世英最烦的是叫他吃饭。他忙起来,啥都不记得。吃饭叫不动,左请右请五六次还不来,好好的热菜热饭,他不吃,放凉了,糊弄吃两口。李世英生气,这几乎是几十年,老两口闹矛盾的唯一导火线。
在单位,他的痴出了名。有人评价,我国得以从无到有,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在研制核潜艇上,仅用10年时间走过国外几十年的路,少不了这份痴气。
1958年,面对超级大国不断施加的核威慑,我国启动研制核潜艇。毛泽东主席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那时,他32岁,因学过造船,又曾搞了几年仿苏式常规潜艇,被选中参加这一绝密项目。
小木屋和摩天大楼都是房子,建起来能一样吗。同样,虽然学过造船,搞核潜艇也是两眼一抹黑。实际上,首批参与研制项目的29人,只有两人吃过点“面包”,核潜艇什么样,大家都见过;里面什么构造,大家都不清楚。
开始论证和设计工作时,他坦言,严格说来,我国缺乏研制核潜艇的基本条件。不论从那个方面看,中国那时候搞核潜艇,在外人看来,都像是一个梦,“简直异想天开”。
一身痴气的他,在科研上是天生的乐观派。他和研发团队一边摸底国内的科研技术,一边寻遍蛛丝马迹,阅读能找到的一切资料,一点一滴积累。他还从“解剖”玩具获取信息。
一次,有人从国外带回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模型。他如获至宝,把玩具拆开、分解,兴奋地发现,里面密密麻麻的设备,竟与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一半靠想象推演出的设计图基本一样。这给了他信心,也挑起了他不服输的倔强:“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设备的基础上发展、创新出来的,没那么神秘。”
他认为自己“不聪明也不太笨”,在核潜艇上做出些成绩,是踏入这个领域,60多年的痴心不改。人来人往,有些人转行,有些人到外地发展;有升官的,有发财的。“我祝贺他们。”他说道,“我还是走自己的独木桥,一生不会动摇。”
小女儿黄峻一语中的:“爸爸这辈子,就是一条道,走到‘亮’。”可不,即便现在走路有时要拄拐杖,他仍然每天从家属楼走到办公室,看材料、想问题。“我还要给年轻人当‘啦啦队’呢。”

黄旭华在中船重工719研究所办公室(11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2)担当的胆识
因与水的摩擦面积最小,水滴线型核潜艇被认为稳定性最好。为实现这一先进的设计,美国人谨慎地走了三步,即先从常规动力水滴线型到核动力常规线型,再到核动力水滴线型。苏联人的步数更多,我国工业技术落后,当时有人提出,保险起见,我们是不是也要多走几步?
“三步并作一步走!”他提出直捣龙潭的大胆想法。我国国力薄弱,核潜艇研制时间紧迫,没钱拖也拖不起。他的决定不是鲁莽得出的:既然别人证明了核潜艇做成水滴型可行,何必要再走弯路?事实证明,他大胆的决策是正确的,也带领团队,的的确确做到了。
他有一套支撑思考的理论:聪明的大脑不在于脑袋有多大,比别人多多少脑细胞,而在于与别人的大脑组成一个头脑网络。倘若把智力用在这个地方,就事半功倍。
潜艇研制涉及专业多,非常复杂。召集大家开会讨论时,他不当裁判,鼓励敞开交流,头脑风暴,这样就把他团队的头脑连成一张网络。综合各方意见,他拍板后,不喜欢再有摇摆。在他眼中,科学上的有些问题几十年争论下来,可能都不会水落石出。只有争一段,横下心来干一段,真相才会明朗。
“干对了,没得说;干错了,我当总师的承担责任。”这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作为核潜艇这么一个大的令人咋舌工程的总设计师,他给同事们的印象很复杂,即可亲又可畏。有时,他像核潜艇,浮在水面,像大海中无穷水滴中最温柔那颗,有说有笑,晚会上还为大家吹口琴,唱流行的歌曲;可一旦潜到工作中,这颗水滴似乎蕴含了无数的能量,像核动力一般前进,不允许有偏航角,并将炮弹精准发向一切障碍。
工作上,他追求完美,有时近乎苛刻。做核潜艇的设计运算时,团队连像样的计算器都没有,只能靠算盘噼里啪啦打出来的。为了保证计算准确,他将研制人员分成两组,分别单独进行计算,只有确保答案一致才能通过,稍有差池,就推倒重算。为了一个数据,算上几日几夜是常有的事。
为确保核潜艇设计和实际运行的一致,他在艇体进口处放一个磅秤,凡是拿进去的东西都一一过秤、登记在册,大小设备件件如此、天天如此。这样的“斤斤计较”,使得这艘核潜艇在下水后的测试值与设计值分毫不差。
1988年初,我国第一代核潜艇迎来大考。它将在南海,开展深潜试验,以检验核潜艇在极限情况下的安全性。在所有试验中,这一次最具风险与挑战。上20世纪60年代,美国王牌核潜艇“长尾鲨”号曾在深潜试验中失事。有些参试官兵中心里没底,有些有点过度的紧张,令人感觉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味道。
他和设计团队与官兵们座谈,讲解核潜艇安全情况,官兵们的紧张得到缓解。就在此时,让在场所有人没料到的是,他当即提出与战士们一起参加试验。此前,从没有过一位核潜艇总设计师亲身参与到极限深潜试验之中。他的身先士卒,打消了战士们最后的顾虑,阴霾一扫而光。
深潜试验成功的那一刻,他不知道为何诗兴大发,即兴挥毫——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
他不喜欢外界把这次深潜,渲染成自己不顾个人安危的悲壮之举。“我们紧张,不是害怕;有风险不是冒险。”他说道,为这次深潜,团队准备了两年,每一台设备、每一块钢板、每一条焊缝、每一根管道,都反复检查、确认,确保万无一失。
这是他的作风,就像在设计核潜艇时一样,他喜欢在前面,把事情做到极致。

黄旭华夫人李世英(右)在为他整理着装(2014年5月28日摄)。新华社记者 熊金超 摄
(3)无言的真情
没参加核潜艇项目研制前,他回到家,母亲拉着他的手说:“你从小就离开家到外面求学,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交通恢复了,社会安定了,父母老了你要常回家看看。”他回答,一定会的。
他成长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他忘不了二哥对他的照顾。他四五岁时,正上小学的二哥,悄悄带他去陪读。回家时,父亲检查二哥功课,二哥一时背不出来,要打二哥,他急了,大声背出来。谁知这一解围使二哥更难堪,挨打更重。二哥没有怪他,第二天依旧开开心心带他去课堂。
他记得,当时调到北京,自己只背了个背包,从此像潜艇一样,“沉”了下去。当时单位领导告诉他,你做的是绝密工作,进来了一辈子就不能出去,就算犯了错误也不能出去,只能留在里面打扫卫生。不能暴露任何信息,成功了一辈子也是无名英雄。
有一次,他被评为劳模,报纸发表时,其他人都有照片,唯独他没有。他的影像保密,就像珍贵文物一样,挂有“请勿拍照”的牌子。
别梦依稀三十载。父母和八个兄弟姐妹,一直不知道他干什么工作,与他只能通过一个信箱联系。父母多次写信问他在哪个单位、在哪里工作,他身不由己,避而不答。
调皮的女儿开玩笑说,爸爸回家就是出差。他回家反倒成了做客,有时候做客还不到一天,就又被长途电话叫走了。
就算回家,他也很少闲下来。技术问题,单位的管理,甚至红白喜事,这些事就像核潜艇内塞满的装备一样,占据了他除睡眠以外的大部分时间。
他曾答应一个女儿,要陪她到北京中山公园看看。几十年后,女儿都有孙子了,他的承诺都没能兑现。
他说这辈子如果有什么遗憾的话,就是欠家人的亲情债太多。父亲病重,他怕组织上为难,忍住没提休假申请;父亲去世,他工作任务正紧,也没能腾出时间奔丧。直至离开人世,老父亲依然不知道他的三儿子到底在做什么。
再后来,他二哥病危,家里发来急电,说二哥想见那位带他上学、替他解围的好弟弟的最后一面。可当时,他日夜忙着重要任务,分身乏术。李世英提醒他,他若不回去,家里人会怨他一辈子,他也会后悔一辈子。但他清楚研发核潜艇,一刻也不能耽搁。他肩上的责任,其他人即便了解,可能也无法解释。他忍痛坚守岗位。
1988年春,趁核潜艇南海深潜试验之机,他携妻顺道看望老母。行前,他给母亲寄了1987年第6期的《上海文汇月刊》杂志。老母亲戴着老花镜,从文章《赫赫而无名的人生》的蛛丝马迹中认定,这篇报告文学的主角“黄总设计师”就是她多年未归的三儿子。
含着泪水看完那篇文章后,他的老母亲把家里的其他兄弟姐妹召集到一起,跟他们讲:“这么多年,三哥的事情,你们要理解,要谅解他。”后来,他听到这句话。他讨厌哭,认为那不是男子汉的样子,可他再也没有忍住。
多年后,他的妹妹告诉他,母亲时不时的找出那篇文章,戴着老花镜认真读,每次她都泪流满面。
与老母亲阔别30年,再重逢时,他也年过花甲。他陪90多岁的老母亲散步,母亲拉着他的手,只字未提他消失30年的事。不断念叨的都是,儿子幼时的趣事,分别时,和30年前一样,嘱咐他常回家看看。
研发核潜艇的工作量是天文般的数字,面对漫长、周而复始,有时找不到头绪的任务,他只能选择百分百的投入。他承认自己只能顾好一头——没有当好丈夫、当好父亲,没有当好儿子,没有尽好兄弟的本分。
这些情债让他至今深感内疚,他的弥补是深沉无言的,就像那条冬天默默陪伴他的围巾。他相信,研制核潜艇,是关系着国家命运的大事。他想,对国家的忠,就是自己对父母最大的孝。通情达理的父母定能体会他的苦衷,他依旧是二老听话的三儿子。说到这里,他觉得自己过得是极好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