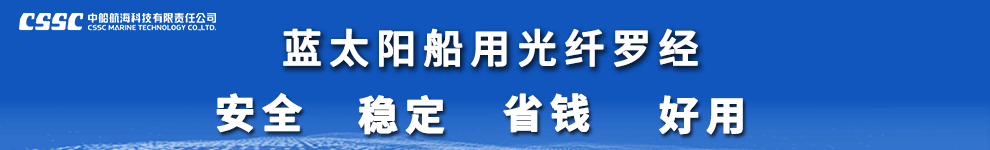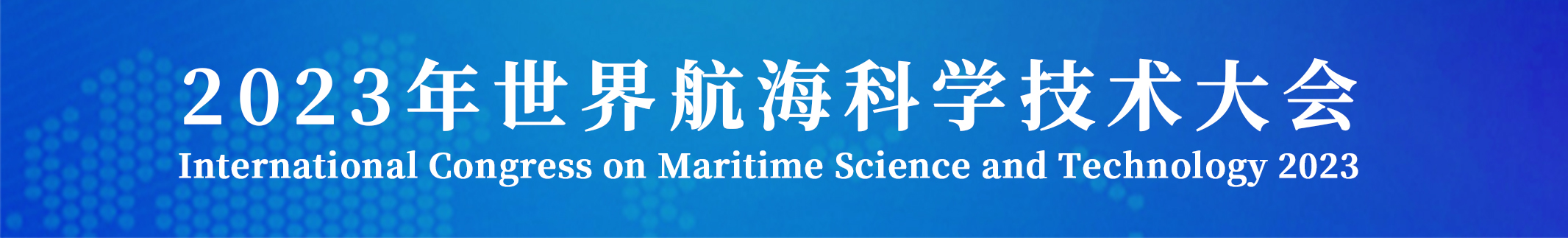五代人守了133年灯塔:眼见太平轮沉海
小叶看着百年来相同的塔光。有时,他似乎理解了爷爷不苟言笑的背后,有着说不尽的孤独,与灯塔剪不断的命运。

叶超群曾经不理解爷爷,那个在孤岛上看守40年灯塔的老人,叶中央。
在岛上的漫长岁月里,老叶给塔里的灯上弦,伴着仅有的海浪、风声与过往的船。
一复一日,“就像是监狱”。
大海曾经把老叶的父亲从礁石上冲走,将妻子和女儿从船上掀入海底。
老叶不认命,在岛上一直待到老。
后来,叶超群也上岛,成了守塔的小叶。那年他25岁,是叶家的第五代灯塔工。 在舟山群岛上,叶家五代人看守灯塔133年,亲历过乘载一千多人的太平轮覆没于眼前,也在孤岛的灯塔里迎接过新生命。
夜晚,光束从塔顶射出,穿透海面数十公里,皎洁硬朗,如月光一般。
这几年,小叶看着百年来相同的塔光。有时,他似乎理解了爷爷不苟言笑的背后,有着说不尽的孤独,与灯塔剪不断的命运。
除了无聊,还是无聊
如今,灯塔所扮演的角色已经渐渐暗淡。
它不再像以前那样,是黑夜中大海的眼睛。过往的船都装了导航系统,甚至用手机地图就可以准确定位。
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船老大,几十年如一日,靠着穿透力极强的光束辨别方向。
在岛上,小叶已经找不到消磨时间的方式了。每天,他检查机器,写写值班记录,定期把所有建筑设备清扫一遍。
如今灯塔值班室里空调、电脑和电视齐全,他把微博、朋友圈刷光了,把《钢铁侠》等漫威电影和美剧也“刷”完了。
日子绵长,时间多得用睡觉也打发不完。岛上的几个灯塔工,除了交班、吃饭时碰个头,人生过往、当下困惑、未来愿景,重重复复地都聊遍了。
被孤独折磨的小叶,无法理解爷爷漫长数十载是如何熬过来的。
那些年在岛上守灯塔,不需要用钟表来感知时间。
娱乐资源极其贫乏,整座岛只有一部收音机,锁在主任的房间里。早晚播一次新闻,台风来临前收听天气预报。
听歌是不被允许的。当时大陆与台湾局势紧张,广播里还能收听到“反攻大陆”的言论。领导留下禁令:“听了这些歌,还工不工作?”
唯一作为消遣的报纸,也是大半个月前送来的。《人民日报》、《浙江日报》,下一艘补给的船还没来,全都读完了。
老叶只能不停地抽烟,在灯塔、在海边、在礁石上,一天抽掉三包。
最初的十年里,目不识丁的老叶自学电机书籍,一个个字对着字典认,字典翻烂了三本。学成之后,他用铜线、铁皮、干电池,制作了一搜银色的登陆艇。
他把登陆艇放进岛上的蓄水池里,看着小艇游来游去,能玩上半天。
他在岛上一待就是11个月。回到县城里,眼见来时的泥土路变成了公路,马车渐渐变成了汽车。
1988年,他坐了几小时船去上海。那是他第一次去大都市,望着车水马龙,呆呆地站在马路边;看着红绿灯变幻,不敢迈出一步。
外面的世界变得太快了。
如今,小叶只需在岛上待一周,就能回家休息一周,日子过得规律舒坦。 三四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小叶开始觉得“压抑”。第一次来岛上,才过了三天,他就待不下去了。
海难如梦魇如宿命
在爷爷老叶的灯塔生涯中,最长一次休假在家,只有三个月。
在人生最长的一次假期前,他失去了至亲的妻子和小女儿。
1971年,妻子带着两个女儿,坐船到岛上要与他团聚。他左顾右盼着期待,最终等来的是一场噩耗。她们那艘摇橹小船,与大船相撞,被风浪掀翻了。
妻子和小女儿丧生,活下来的女儿,智力受损。这成了老叶心底最大的痛。
这种痛并不陌生,仿佛某种命运的轮回。在他5岁那年,也是海风猛烈的夜晚,海岛附近的一艘船上,一老一小困在翻滚的浪里,靠不了岸。
老叶的父亲向海边礁石走去,一阵大浪拍向了他。
七十多年后,叶中央还清楚地记得父亲被海浪带走的位置。 图/杨宙
那是父亲留给老叶最后的背影。如今,76岁的叶中央还记得深邃大海里,那个模模糊糊的物体,在海里无助地飘着,飘远了。天色欲亮,母亲哇哇的哭声回响耳边。
遗体打捞上来后,他一眼认出了父亲腰上紧绑着的腰带。
海难的记忆就如梦魇如宿命,纠缠老叶的一生。
“一般来说5岁的时候记不了那么多东西。但是我记得很清楚,意味着父亲没有了。”71年后,叶中央用吃力的舟山普通话,努力地表达每一个词,向外人拼凑关于父亲的最后一点回忆。
小叶曾经不知道这些伤心的家族往事。他儿时的记忆里,也有一艘船。
船把他从海这头的宁波镇海,送到了那一边的舟山嵊泗。背着小书包的他,独自一个人坐在船上。那似乎是童年的常态。
幼儿园里,他看着小朋友们被爷爷奶奶接走,然后自己一个人,走过两三个路口回家。爷爷从来没对他笑过,更别说买零食买玩具。
除了来镇海开会或看病,爷孙俩很少见面。他知道爷爷在灯塔,可灯塔上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奶奶哪去了?他从来不问。
镇海与嵊泗之间,海水潮起潮落,横亘在相距两地的爷孙之间。
往昔似乎难以在亲人间提起。直到小叶自己也当上了灯塔工,在单位的宣传讲座上看到爷爷的采访视频。从影像资料里,他找到奶奶的去踪,填补上缺失的亲情记忆。
小叶后来才知道,曾经不断有人劝爷爷别再上灯塔工作了,但老叶不理睬。
已经分不清是别无选择还是固执坚守。多年后,孙子这样理解爷爷,“他不是为了守这个灯塔,而是为守这个责任,守这份对亲人的歉疚。他想偿还这些东西,不然正常人很难去坚持。”
从大江大海到行将搁浅
小叶没有想过自己可以长久地坚持下去。起初,灯塔这份工作对他而言,是一种“无所谓”的选择。
那会儿,他在舟山有一份工作。每次放假回家,爸爸总做爷爷的传声筒:去守灯塔吧。
被“催眠”了大半年,他辞了工作,上了海岛。
出生于1988年的叶超群,身处的时代是自动化操作、便捷的联络与运输,哪里还有大江大海般的历史故事?
那些记忆属于爷爷和爷爷的爷爷。67年前的那个除夕夜前夕,从白节山灯塔值班回来的老叶说,一艘客轮沉没了。
那是太平轮。国共内战后,国民党军队溃败,陆续有人从上海跑到台湾。搭乘那班船的,有当时的很多名人,比如蒋经国的好友,袁世凯的孙子,还有神探李昌钰之父和亚洲女首富龚心如之父,等等。
在白节山附近的海域,黑夜中熄灯急驶的太平轮与从台湾基隆开往上海的货轮相撞。两船相继沉没,近千人罹难。 那一晚,叶中央的爷爷在白节山灯塔上,看着远处闪烁着的满船灯光,沉没于一瞬。
凌晨三四点后,岛上的渔民摇撸到远处寻找,茫茫大海里什么也没有了。
许多皮箱飘到了白节山岛上,那是整箱整箱的衣服,还有包装精致严密的白色粉末。村民舔了口,不是面粉。
有些箱子里,装着一堆白纸,纸上印着一串串数字。纸张细滑丝薄,小孩拿来当草纸用,还嫌太滑溜。
向城里的人一打听,才知道那一沓沓的,都是上海汇丰银行白花花的支票。
整箱的白色票子,被废弃摊放在白节山岛上,风吹日晒。在白纸的随风飘散中,一个唏嘘的时代过去了。
和平年代里,也有小风小浪的颂歌。有一年,老叶同事的妻子怀着身孕,上岛看望丈夫,突然腹痛临盆。在来不及送回县里和派医生上岛的情况下,他们靠着两个电话,将妇产科医生的“战术指导”,一声传一声,喊进在海岛上接生的老叶耳里。
后来,他们把那个在灯塔上出生的女孩,取名为灯礁。
到小叶的父亲叶静虎那一代,虽然在岛上的时间远比爷爷短,倒也能说出一些艰苦卓绝的故事。
比如,为了对抗炎夏,他们露天铺席子睡觉。虫子渗进了肉里,像钉子钻了进去,吸血后从芝麻变成了绿豆大。手指猛地一拔头尖,躯体还留在肉里。
再平淡乏味,也有遍地的蛇与蜈蚣作战,还有漫天的星光银河,和在海岛上仰望牛郎织女星。
故事到了叶超群这一代,就行将搁浅了。生活平淡如流水,哪里还有什么刻骨铭心的坚守。
欲望年代的纯真孤岛
岛上的生活处处无聊,可伤心之处往往在陆地上。
实习时领着微薄的工资,小叶处处看人脸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出去相亲时,被问及房子车子,看长相看家庭。
相比之下,岛上人人平等,需求简单,毫无纠葛。在这个80后眼里,欲望年代里,那些守灯塔的地方,是“纯真的孤岛”。
回不到爷爷对抗孤独的单纯生活了。从前都是慢的,时间流逝于海平线升起的朝阳、正午时孤岛上消失的影子,和另一边海平线上消逝的夕阳。
有时船儿经过,拉响三声汽笛。灯塔工听见,跑到国旗下,升降三次旗,用无声的问候回应对方。
叶超群值守的七里屿,距离宁波港不远,海水泛黄。
如今,小叶被分配在七里屿,距离宁波港40多分钟船程的岛上。港口的泥沙冲入海里还未平息,小岛被浑黄的海水包围着。
舟山群岛成了旅游旺地。电影《后会无期》在舟山的东极岛取景拍摄后,游客爆棚。岛上采取措施,将每天的客船票数限制在1600张。
为了上岛,有些游客从凌晨1点就开始拿着板凳,排队买票。
他们向往海岛上的文艺景色,如同电影里《东极岛岛歌》唱的,“东极岛/你是人间的仙境/太平洋的阳光它最先照耀这里”。
事实上,小叶觉得爷爷和父亲守灯塔时待过的岛更美好。
单位没把叶超群派到父辈的岛上。近两年经费少了,又赶上媒体大批大批地前来报道,把他安插在宁波附近的七里屿,采访起来也省钱省力。
老叶跟小叶说,在他待过的岛上,趴在床上能听见来自海底的声音。他鼓着嘴模仿大鱼小鱼的不同叫声。大鱼咕——咕,小鱼咕咕咕,像地里的青蛙。
岛屿下方,有千万条鱼,在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