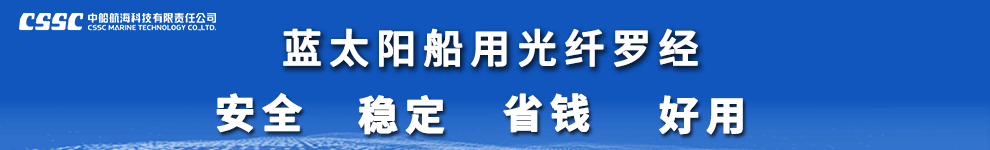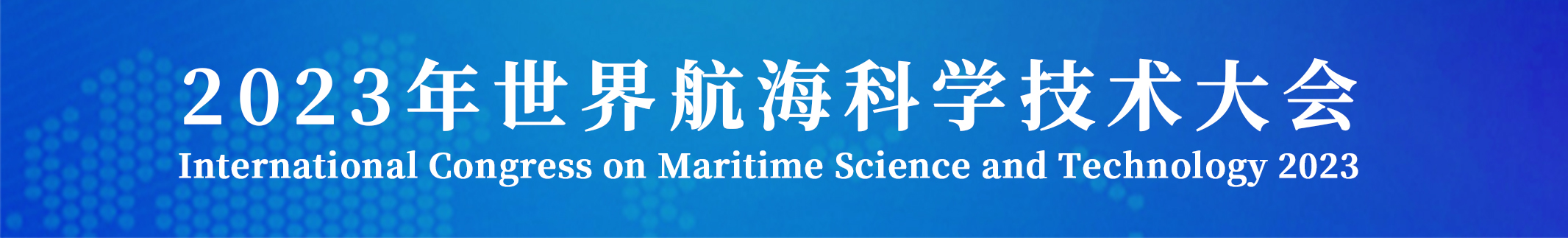中国企业如何应对禁诉令(anti suit injunction)?
【提要】近日,武汉海事法院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高等法院(香港法院)作出的禁诉令(anti suit injunction,也称止诉禁令)出具了一份裁定书((2017)鄂72行保3号),在该裁定书中,法院准许请求人某保险公司提出的海事强制令申请,以海事强制令的形式责令被申请人向香港法院申请撤回禁诉令。国内法院以往对于外国或香港法院禁诉令大多持置之不理的态度,武汉海事法院主动出击回应尚属首例,日后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法院变消极为主动,以彰显司法管辖权。本文将对该案例进行评析,主要介绍禁诉令的依据、针对中国诉讼的禁诉令及其后果与应对,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法院签发禁诉令的可能性。
案情介绍
2017年6月2日,某保险公司(即海事强制令申请人)以某租船公司(强制令被申请人,注册地址为希腊比雷埃夫斯)就VC00818号提单(由“KEN SIRIUS”轮承运)所涉海上货物运输纠纷为由,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诉前海事请求保全,要求扣押租船公司所属船舶(该船舶停泊于中国镇江港),武汉海事法院裁定准许扣船。
2017年6月8日,保险公司以海上货物运输提单纠纷为由,向武汉海事法院起诉租船公司,请求法院判令租船公司赔偿损失并承担法律费用。武汉海事法院立案受理,并于2017年6月9日向该案被告租船公司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文书。
租船公司以上述案件存在仲裁条款为由,向香港法院申请禁诉令获得准许。2017年6月29日,香港法院签发禁诉令,责令保险公司撤回上述起诉,或禁止保险公司就与VC00818号提单包含或证明的运输合同项下产生的任何纠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启动任何进一步或针对租船公司的诉讼程序。
保险公司因此向武汉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要求该院责令租船公司向香港法院申请撤回禁诉令,并向法院提供了由另一保险公司提供的保证担保。
武汉海事法院经审理认为其已根据诉前保全(扣船)程序取得管辖权,租船公司收到法院文书后未在答辩期内提出有效的管辖权异议。因此其向香港法院申请禁诉令的行为侵犯了保险公司的合法权益,因此裁定:1、准许保险公司提出的海事强制令申请;2、责令租船公司立即向香港法院申请撤回禁诉令。
二、评析
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平行诉讼以及解决管辖权的冲突,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措施,于是以英美法系国家为代表的禁诉令制度应运而生。禁诉令是指在一定条件下,由本国法院签发的、限制在本国的原告在某一外国法院实施相应的法律救济措施的一项强制令,是英美法系国家常用的一种对抗挑选法院和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措施,禁诉令制度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
1、禁诉令的依据
禁诉令制度起源于14世纪的英国。它最初是英国用于解决国内平行诉讼的手段。在早期的英格兰,王室法院和教会法院之间存在管辖权上的重叠,王室法院常用禁诉令限制当事人在教会法院诉讼。禁诉令也被衡平法院用于与普通法院争夺管辖权。如果衡平法院认为由普通法院审理不合适,就可以向普通法院诉讼中的原告发出禁诉令。这种解决国内平行诉讼的方法后来被英国用于解决国际平行诉讼。
目前英国法院作出禁诉令的权力是基于英国《1981年最高法院法》(“the Supreme Court Act 1981”)的规定,该法第37条第1项规定:
“高等法院可以命令方式(无论是中间的还是最后的)作出禁令或指定接收人在所有法院认为这样做是公平和方便的案件里。”(“The High Court may by order (whether interlocutory or final) grant an injunction or appoint a receiver in all cases in which it appears to the court to be just and convenient to do so.”)
英国《1996年仲裁法》也明确规定英国法院为协助仲裁有同样作出禁诉令的权力,该法第44条“法院为协助仲裁可行使的权力”(“Court powers exercisable in support of arbitral proceedings”)规定:
“(1)除非当事人另有不同约定,为了仲裁目的法院在与仲裁有关事项具有同样的权力作出以下命令。包括:......(e)作出中间禁令......”(“(1)Unless otherwise agreed by the parties, the court has for the purposes of and in relation to arbitral proceedings the same power of making orders, Those matters are:......(e) the granting of an interim injunction...”)
2、禁诉令的适用范围
依据Allianz SpA v West Tankers Inc (CaseC-185/07)案(“Front Comor”案),缔约国法院不得在欧盟范围内发出禁诉令阻止其他的诉讼程序,即便此种程序与仲裁协议相违背。在该案中,关于英国法院针对仲裁协议作出的禁诉令是否违反欧盟《民商事管辖和承认与执行判决规则》(“《布鲁塞尔规则》”),欧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认为,尽管仲裁不属于欧盟《布鲁塞尔规则》所规定的范围,但是在海外所发起的诉讼程序却属于《布鲁塞尔规则》规定的范围,因此,英国法院所作出的禁诉令构成了对外国法院司法主权的干涉,这是不允许的,也违背了《布鲁塞尔规则》所规定的互惠和礼让法律原则。
虽然英国法院的禁诉令制度在“Front Comor”案中遭受重大冲击,但是这并不影响英国法院寻找其他的途径支持仲裁协议,并在欧盟范围之外继续行使发出禁诉令的宽泛自由裁量权。
在英国最高法院2013年的Ust-KamenogorskHydropower Plant JSC v AES Ust-Kamenogorsk Hydropower Plant LLP ([2013] UKSC 35)一案中,双方的仲裁协议约定以ICC仲裁规则在伦敦仲裁。随后,仲裁协议被哈萨克斯坦最高法院判决无效。JSC公司在哈萨克斯坦法院起诉AES公司要求提供相关信息,AES公司以双方存在仲裁协议为由向法院申请中止诉讼程序,而法院则以仲裁协议已经被判决无效驳回了AES公司的申请。
由于本案发生在欧盟范围之外,AES公司成功向英国法院提起申请禁诉令的程序。而JSC公司则以双方还没有在英国进行仲裁程序,英国法院没有做出禁诉令的管辖权为由提出挑战。法院驳回了JSC公司的抗辩并指出,仲裁程序尚未进行或无意进行都不能限制或限定英国法院对违反仲裁协议已经进行或意图进行的法院程序行使禁令的一般权力。换句话而言,即便英国国内没有互为冲突的仲裁程序正在进行之中,英国法院也可以对非欧盟法院的诉讼程序发出禁诉令。
在 Joint Stock Asset ManagementCompany “Ingosstrakh-Investments” v BNP Paribas SA [2011] EWCA Civ 644一案中,BNP与另一家俄罗斯公司俄罗斯机械公司(Russian Machines)订立了一份保函。保函适用的是英国法并约定了在伦敦仲裁。BNP与俄罗斯机械就保函发生争议,BNP提起仲裁请求执行该保函,而俄罗斯机械公司对保函的效力予以否认。与此同时,Ingosstrakh-Investments公司几乎同时在俄罗斯起诉,申请法院判令该保函无效,并将俄罗斯机械公司列为被告。
BNP公司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禁诉令,以俄罗斯机械和Ingosstrakh-Investments公司合谋为由,阻止两家公司进一步参与俄罗斯法院的程序。高等法院同意了BNP的申请,Ingosstrakh-Investments公司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本案的独特之处在于,BNP所申请的禁诉令,不仅针对的是仲裁协议的当事方,还针对非仲裁协议的当事方。上诉法院在考虑了两家俄罗斯公司的持有人相同、交易的重要性、仲裁和俄罗斯法院程序、Ingosstrakh-Investments公司提起俄罗斯法院程序的时间点及其不具有单独行动的可能性这些因素之后认为,在俄罗斯法院所进行的程序是为了阻止仲裁程序的进行。因此,上诉法院维持了高等法院作出的禁诉令,Ingosstrakh-Investments公司和俄罗斯机械公司都不得参与俄罗斯法院的程序。
因此可知,英国禁诉令在欧盟内是无效的,但是英国法院仍可以对欧盟以外的国家的法院诉讼做出禁诉令,而我国当事人/企业仍会面临英国禁诉令的威胁。
3、近年来针对中国诉讼的禁诉令
1)西霞口案((2016)最高法民再15号)
2006年,荣成市西霞口船业有限公司(“西霞口公司”)作为卖方同荷兰西福特船运公司(“西福特公司”)签订了船舶建造合同,并在补充协议中约定“船用主机必须使用瓦锡兰主机”。根据此协议,西霞口公司同瓦锡兰芬兰有限公司(“瓦锡兰芬兰”)签订了订购船舶主机的买卖合同。其中西霞口公司西特福公司的合同约定伦敦仲裁,西霞口公司与瓦锡兰芬兰之间的协议约定巴黎仲裁。由于西霞口公司没有能够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交船,西福特公司先后取消了两份合同,并在伦敦提起仲裁,仲裁庭裁定西福特公司解除合同有效,西霞口公司应当返还预付款。
在伦敦仲裁期间,西霞口公司在青岛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西福特公司和瓦锡兰芬兰合谋提供了二手主机,导致船试航时验收不合格,其行为构成了共同侵权,应当赔偿损失。(注:西霞口船业企图通过诉西福特公司及瓦锡兰上海公司共同侵权,试图以共同侵权突破仲裁管辖。对于管辖权异议,一审和二审法院均认为西霞口公司分别与西福特公司、瓦锡兰芬兰之间的仲裁条款均不足以涵盖涉案争议的问题,故仲裁条款不具有约束力,最高院在再审裁定中确认中国法院的管辖权。但在国内诉讼程序中,最高院最终认为两公司不存在共同故意,因此对西霞口公司的侵权索赔未予支持)。
该案中同时出现伦敦仲裁程序和国内诉讼程序,为了避免该案在中国境内诉讼,西福特公司向英国法院申请了禁诉令(anti suit injunction),禁止西霞口公司在中国进行的诉讼。该禁令送达后,西霞口公司并未理会,中国境内诉讼也并未因此受到影响。
2)“FORTUNECLOVER”轮案
2011年8月10日,白长春花公司所属的“FORTUNECLOVER”轮装运大豆从巴西桑托斯运南通港,收货人红蜻蜓公司持有船东出具的正本提单提货时,南通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出具《品质检验证书》载明大豆不符合买卖合同要求,红蜻蜓公司起诉向承运人白长春花公司索赔。
白长春花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涉案纠纷应提交伦敦仲裁。其认为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条、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五十八条、《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一)项(甲)等项规定,仲裁条款的效力审查应适用仲裁地法律即英国法;涉案提单(康金1994格式提单)注明需与租约一同使用,且提单条款写明租约中的仲裁条款及法律适用条款都被并入该提单,根据英国法的规定,伦敦仲裁条款有效。
为了避免在中国境内陷入诉讼程序,白长春花公司向英国高等法院申请禁诉令,英国高等法院Cooke法官于2012年12月18日下达禁诉令,并于2013年3月8日做出继续禁诉令,明确所有与涉案提单所证明的运输合同相关的争议应在伦敦通过仲裁解决。2015年4月22日,伦敦仲裁庭作出仲裁裁决。
2015年12月14日,湖北省高院维持了武汉海事法院驳回白长春花公司管辖权异议的裁定,虽然在裁定书中提及禁诉令,但未作任何评价,直接予以忽略。
3)“NORD LUNA”案
在M/V“NORD LUNA”案之中,因卸货过程中发生货损,中国收货人厦门A公司在厦门海事法院对船东B公司提起诉讼。船东提起管辖异议,认为案件应该在伦敦仲裁。海事法院最终以该案双方并非所涉航次租约当事人,因此提单并入的租约仲裁条款不能有效并入,也不能对双方产生拘束力。
船东同时启动伦敦仲裁,并申请英国法院签发禁诉令,禁止A公司在厦门海事法院继续对船东提起诉讼,关于英国法院禁诉令的效力,最高法院在(2010)民四他字第67号批复中认为,B公司主张以伦敦高等法院的禁诉令作为英国仲裁庭确定双方存在仲裁协议的依据,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虽然最高院没有直接对英国法院禁诉令效力表态,但基本实质性的否定了其效力。
4)“新泰海”案
2011年7月29日,“新泰海”轮与“B Oceania”轮在马六甲海峡南部海域发生碰撞,造成后者连同船上满载的矿砂沉没。新泰海轮向青岛海事法院申请设立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而“B Oceania”轮在青岛海事法院登记了债权,并于半年后趁新泰海轮到达澳大利亚之际,申请扣船并对其提起对物诉讼。
2012年5月10日,澳大利亚联邦法院接受“新泰海”轮担保函,并解除对新泰海轮的扣押。当日,青岛海事法院裁定准许“新泰海”轮的申请,发布“海事强制令”,“命令”“B Oceania”轮船东:“立即解除在澳大利亚对申请人所属的船舶‘新泰海’轮的扣押,并在今后不得对申请人的人和财产行使扣押或其他妨碍措施。”
随后,青岛海事法院在裁定驳回对“海事强制令”的复议申请中进一步说明,即使“海事强制令”中的解除扣押的命令已经没有执行的必要,“B Oceania”轮船东“不放弃新泰海船东提供的担保”仍属强制令所述的“妨碍措施”,是违反海事强制令和中国程序法的行为,必须予以纠正。
为了保住手中的担保,“B Oceania”轮向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申请,并最终获得禁诉令,该禁令要求要求“新泰海”轮船东不得继续在中国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程序,应立即向青岛海事法院撤回强制退回保函的强制令申请,并采取一切措施撤回或放弃执行回收保函。
青岛海事法院发布的“海事强制令”未得到执行,随即“新泰海”轮以中国法院先受诉且已设立责任限制基金为由向联邦法院申请中止诉讼,联邦法院认为该院无“明显不适合管辖”,驳回了申请。该案最终以和解结案。
5)“Long Charity”轮案
2009年7月31日“Long Charity”轮装载铁矿石货物从南非装货港出发,驶往目的地中国鲅鱼圈港,开航不久,因发生故障而搁浅,后经荷兰救助人成功救助,部分货物卸下转运,部分货物随原船在拖轮护航下完成航次。该批货物中国买方持有正本指示提单,在大连海事法院对船东GARLINGFORD LIMITED提起货损索赔之诉。
船东在大连海事法院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提单并入了租约仲裁条款,中国法院无管辖权。不久,船东又指定了伦敦仲裁员并向英国法院申请取得“禁诉令”(Anti Suit Injunction),命令中国收货人不得继续在中国国内的诉讼。但我国外交部拒绝协助向中国收货人送达该禁诉令。关于船东在大连海事法院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法院裁定提单没有有效并入租约仲裁条款,提单持有人与船东之间不存在提交仲裁的合意,中国法院具有管辖权。
4、违反禁诉令的后果
禁诉令直接针对已经或将要在英国以外的他国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人,禁止权利人在他国法院开始或继续诉讼。不承认并不代表禁诉令对当事人不具有效力,如果当事人在英国无利益可言,那么可以忽略禁诉令的存在,反之,则需要认真对待。
如上所述,虽然英国禁诉令在欧盟内是无效的,但是英国法院仍可以对欧盟以外的国家的法院诉讼做出禁诉令,因此,我国当事人仍会面临英国禁诉令的威胁。违反禁诉令将被视为藐视英国法庭,违反者将面临严重惩罚,包括监禁或在英国的财产被扣押等等。且违反者将会承担所获得的外国判决在英国得不到承认和执行的不利后果。此外,英国法院签发的禁诉令通常是永久性的,违反该命令的当事人将永远不得涉足英国,除非其自愿接受惩罚。显然,禁诉令对于当事人的威慑力往往取决于签发禁诉令的国家与禁诉令所针对的当事人之间的关联是否密切。
据了解,国内某保险公司领导因未执行禁诉令的要求,在其到伦敦出差期间,险被英国法院拘留,后来发现英国法院禁诉令将该领导的姓名写错,才得以未被执行拘留。上述“KEN SIRIUS”轮案中,香港法院作出的禁诉令未被遵守,如果禁诉令上记载的该保险公司领导前往香港,则可能被香港法院以藐视法庭等为由进行惩罚。
由于我国不少大型企业在海外有分支机构,如中国银行在英国就有分支机构,如果该企业不理会英国法院发布的禁诉令,则英国法院可能对其分支机构采取强制措施。
5、禁诉令的应对
目前国内法院、当事人大多以不予理睬、不予认可等方式对待禁诉令,但消极处理不能避免承担违反禁诉令处罚的风险,尤其是出现在作出禁诉令法院所在国家/地区的领土时。
针对禁诉令,我国当事人可以以不存在有效仲裁协议为由向英国高等法院商事法庭申请撤销禁诉令,商事法庭将根据合同的准据法来审查合同中是否存在仲裁协议。由于英国法律对仲裁协议解释非常宽松,否定仲裁协议进而撤销禁诉令非常困难。
2016年1月12日,在中国银行与某船东的案件中,因香港高等法院针对中国银行作出禁诉令,中国银行以申请人严重延迟申请禁诉令及禁诉令可能侵犯或妨碍中国司法主权为依据向香港法院撤销禁诉令。最终香港高等法院颁下书面判词,撤销了案件申请人(某载货船舶船主)对中国银行发起的禁诉令申请,并下令案件申请人需要缴付客户的讼费(包括大律师的费用),保障了中国银行的分行可继续在内地行使其诉讼权利。
上述“KEN SIRIUS”也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应对措施,即通过向海事法院申请“海事强制令”,“命令”被申请人向作出禁诉令的法院申请撤销该禁诉令。当然,该途径是否能有效执行尚未确定,由于我国缺乏“藐视法庭”等处罚制度,则即使被申请人拒绝申请撤销,也缺乏相应制约措施。另,即使被申请人举证证明其已经申请撤销,该申请是否最终能得到香港法院准许,即是否以成功撤销作为遵守海事强制令的标准,均未在法院作出的海事强制令中得到明确。
另外,如果选择遵守禁诉令,停止在中国的诉讼程序,转而通过仲裁程序解决,则应注意仲裁时效的规定(例如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向承运人索赔时效一年)。为了保住仲裁时效,可以在英国法院应诉禁诉令案件时请求法院在准予禁诉令的同时给予时效延展。对索赔人在我国法院开始的诉讼程序,若国外当事人以存在有效仲裁协议为由提出管辖权异议,则应催促我国法院及时对管辖权争议做出裁决,以尽早确定是否放弃法院管辖,以免当事人耽误仲裁时效。
6、中国法院能否做出禁诉令
禁诉令制度对于解决国际管辖权冲突以及协调国际平行诉讼起着非常有力的作用,虽然这一制度在国际平行诉讼的司法实践中饱受争议,但禁诉令是解决国际民事诉讼管辖权冲突与协调国际平行诉讼的一种有效方式,在国际平行诉讼中能表明本国维护其司法管辖权的态度与立场。
中国目前没有关于禁诉令的规定,但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五十一条,海事法院可以发布海事强制令以责令被请求人作出或者不作为的强制措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海事强制令可以起到上述禁诉令的效果。
如“新泰海”轮案中,应“新泰海”轮船东申请,青岛海事法院发布“海事强制令”,“命令”对方船东“立即解除在澳大利亚对申请人所属的船舶新泰海轮的扣押,并在今后不得对申请人的人和财产行使扣押或其他妨碍措施。”随后,该院进一步说明,对方船东船东“不放弃新泰海船东提供的担保”属强制令所述的“妨碍措施”。
在上述“KEN SIRIUS”轮案中,武汉海事法院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五十一条作出责令租船公司立即向香港法院申请撤回禁诉令的裁定,与“新泰海”轮案中青岛海事法院在“海事强制令”中要求解除扣押、退还担保类似。
青岛海事法院在“新泰海”轮案中还“命令”对方船东“在今后不得对申请人的人和财产行使扣押或其他妨碍措施”,即相当于责令对方船东采取不作为的强制措施,这便与英美法系禁诉令的表述类似。由此,笔者认为,海事法院通过海事强制令责令被申请人“不得在其他法院/仲裁地提起针对申请人的诉讼或仲裁程序”完全符合海事强制令的法律含义,只是时间问题,而不是技术问题。
参考文献:
中国式禁诉令及其在涉外海事司法之中的运用,彭先伟,德恒律师事务所微信公众号,2016年12月1日;
从“西霞口”案看中国造船厂在造船合同纠纷中面临的法律问题,蓝天,海商法资讯微信公众号,2017年4月14日;
英国禁诉令的最新发展,汪鹏南,海事商事法律报告lCMCLR微信公众号,2016年12月6日;
中国企业或个人收到英国法院的禁诉令该如何应对?潘辉文,英国法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2016年10月19日;
余硕,浅析国际平行诉讼中的禁诉令制度,《法制与经济旬刊》,2013年12月;
中澳法院对平行诉讼的处理方式比较——“新泰海”轮案,邱宇灏,http://www.wjnco.com/cn/articles_show.asp?Articles_id=265,2017年7月23日21:06时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