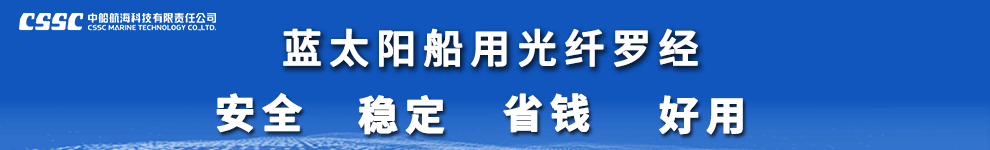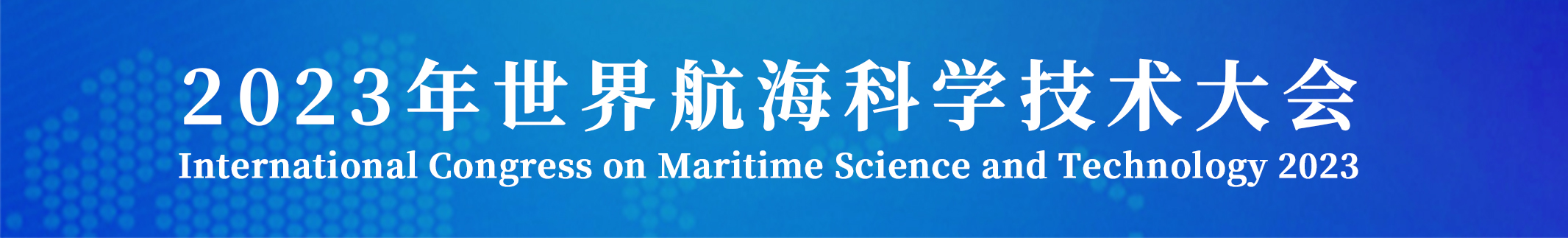面向海洋的秦汉文化——评《秦汉海洋文化研究》
地球以地为名,然而陆地所占不过地球表面三分之一,超过三分之二的地球表面是被海洋所覆盖的。这一命名模式,实际上体现着人类基于自身历史的认知倾向。
相比于人类能够直接感知并长期赖以生存的陆地,在地理知识和世界知识尚未充分发展的历史时期,海洋无法为人所认知,因而代表着未知和虚空。如英国约翰·迈克在《海洋:一部文化史》中所述,“就其构造而言,大海是空洞的,是一个不是地方的地方”“大海没有历史,至少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事实上是一种荒蛮的混沌和无序状态”。中国文化名人屈原曾有震撼人心的《天问》,其中“八柱何当,东南何亏”一句,将分布在我国东南的茫茫大海视作陆地缺损的虚无之处。若追寻最初字义,则会发现“海”的本义源自“晦”,取其昏暗晦黑之意。《释名·释水》有:“海,晦也,主承秽浊,其色黑而晦也。”《博物志》有:“海之言,晦昏无所睹也。”所指向的,是海的幽冥。
但海洋并非没有历史,海洋史作为一门学科,在近几十年中已经有了长足发展。海洋以其彼此连通的特性,使世界有了成为一体的可能。因此,海洋史被视作全球史研究的有效路径之一。
中国史研究先天缺乏关注海洋的动机。文明的形成、历史的面貌,和地理条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与地中海文明所面对的被海洋分隔的“破碎的”陆地不同的是,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我国以土地的广袤辽阔,以陆地的完整独立,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中华文明。但不能因此忽视海洋。我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在认识海洋、探索海洋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海洋文化,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华文明向东方、南方的传播,也有赖于海上航线的开辟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中国人的地理知识和世界知识,正是随着对海洋的探索而逐步完善的。在中国史研究中引入海洋史观自有其必要性。
王子今教授新著《秦汉海洋文化研究》,即是在秦汉史领域做出的有益探索。海洋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涵盖面极其广泛的综合概念,其中既涉及物质文化,也涉及政治文化与精神文化等;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海洋文化进行研究,则涉及政治史、交通史、文化史、思想史、经济史、科技史、军事史等诸多层面。作者深耕秦汉史领域数十年,此番以六十万字专著描绘面向海洋的秦汉文化,是建立在对秦汉历史和文化的充分掌握之上,跳出陆地史观的全新尝试。
全书体例完备,内容丰富,涉及秦汉海洋文化的方方面面。作者以其开阔的学术视野,广泛搜罗史料,进行跨学科的综合考察,深入历史的细微处,以小见大,多有开拓之功。在空间上,既关注作为通道的海面,也关注沿岸的海港;在交通上,既关注海滨的“并海”之行,也关注海上航路的开辟;在行政上,既关注沿海的区域控制,也关注海洋的资源开发;在海洋学上,既关注海洋生态与灾害,也关注“海中星占”;在物产上,既关注丰饶的鱼盐之利,也关注新奇的海洋生物,既关注作为能源的海底“泥油”,也关注作为珍宝的“珠玑”“玳瑁”;在人群上,既关注秦皇汉武,也关注方士和将军,既关注以海为生的“海人”与“习船者”,也关注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亡人”与“海贼”……凡此种种,难以尽述。
将古代的海洋作为历史空间进行描述殊非易事。海洋以其不断的流动,以其难寻边界的宽广无垠,共同宣示着一种难以为人所控制的无序状态。这种不可知性和不可控感,激发了古人的奇崛想象,滋生出独具魅力的神秘文化。秦汉方士所描绘的海洋世界,是仙人所居、奇药之属,又有符命祥瑞,萦绕在海面的氤氲水汽之上。这都令秦汉帝王魂牵梦绕。秦皇汉武之日常所居毕竟远离海滨,但无论是他们屡次“并海”而行和“东巡海上”,还是秦始皇陵内“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的海洋构想,汉武帝在宫殿区营造的“海池”与“海中神山”意象,所共同体现的,都是一种强烈的海洋情结,是对海洋的憧憬与向往。秦汉时期的海洋探索,就一定程度上建立在这种憧憬与向往之上。前有徐福为秦始皇东渡入海寻仙药,后有东方朔谏止汉武帝“欲自赴海求蓬莱”。面向海洋,秦汉帝王所求有二,一是希求长生不老,二是祈望预知政治气运。这些在科学原则下看似荒诞不经的追求,却在客观上促进了海洋资源的开发、航海技术的进步、海洋航路的开辟和海外联系的初步扩展。这种理性与非理性的交织、想象力与实用主义的缠绕,共同构建起秦汉时期海洋文化独具特色的历史风貌。
在秦汉人的心目中,海洋既是仙居,也是险地。直面未知的海洋,本就需要过人的勇气;对海洋的探索与开发,更伴随着重重危险。在面向海洋的文化表现中,秦汉人以其锐意进取的开创精神、实用主义的科学精神、不畏艰险的英雄主义精神,展现着积极的时代特色。在这样昂扬的时代风貌中,无数秦汉人携手前行,前赴后继,共同谱写了面向海洋波澜壮阔的秦汉历史。时至今日,仍然有着触动人心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