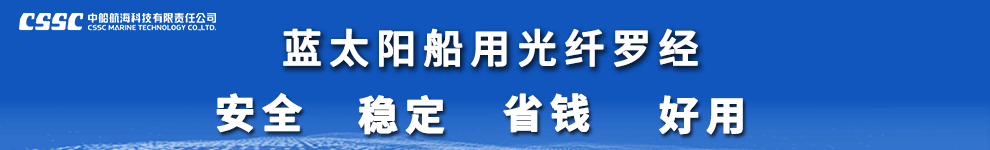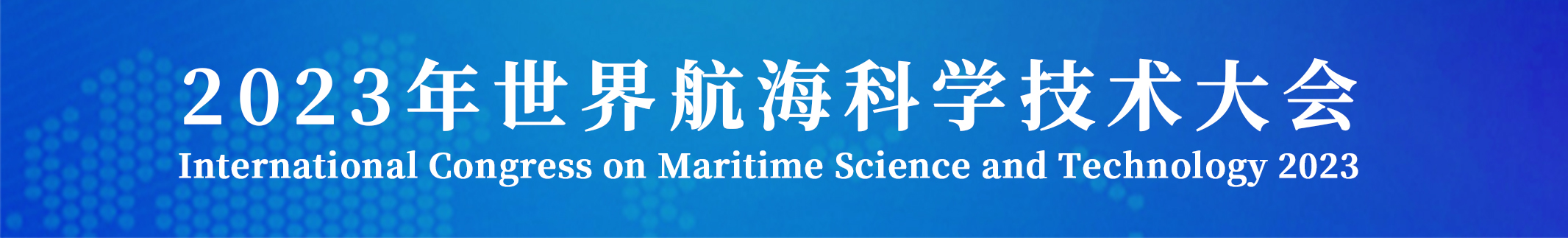唐代扬州——得水独厚吞吐天下的江海巨港
江海合一的巨港
扬州的繁华,完全是因港而兴。没有长江、大海与南北运河,便没有扬州大港;没有吞纳天下的巨型港口,岂有繁华美丽的扬州?唐时的扬州,“……东至海陵界九十八里,又自海陵东至海一百七里”,恰居于当时东部沿海长江三角洲的中心。这样的地理优势,诗人们用形象思维的方式,给予了艺术的表达。唐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秋天李白首次畅游扬州,登高眺运时,便将他的所见在《秋日登扬州西灵塔》一诗中吟出:“宝塔凌苍苍,登攀览四荒。顶高元气合,标出海云长。……目随征路断,心随去帆扬。”这是诗人高瞻远瞩时所捕捉到的海云飞飘,征帆出港疾去的画面。后来李绅到了扬州,也有《宿瓜州》的题吟:“烟昏水郭津亭晚,迴望金陵若动摇……”他经长江而来,船泊定了,大江就在身边流过,金陵却也似乎随着江涛在动荡。后来他的征帆虽已进入了泗水之口,却仍在念念地低声唱着“烟树寂寥分楚泽,海云明灭满扬州……”其后罗隐在《广陵开元寺阁上作》一诗里,吟出他所见到的扬州港口是:“……江蹙海门帆散去,地吞淮口树相依。”这里,诗人们所目睹的,正是江尽海开之处,一幅幅巨帆竞发的壮观港景。如此,长江带系着扬州;大海潮涌着扬州;运河和淮汴缠绕着扬州。它如此的得水独厚,完全具备了经营长江、运河、海洋舟船运输的综合型大港的良好条件。因此,扬州才经常是八方辐凑,舳舻群集。
据《雍正重修扬州府志》记载,扬州“上自六合界,东至仪征小帆山入境,绵延数十里,接江都界,迤逦正东北四十余里,至官河水际而微其脉”。勾画的就是扬州港区的水域范围。当时的瓜步与瓜洲,内港的通道是两座最大的具有吞吐江艑、海舶功能的江海汇合的外港区域。初唐时的骆宾王大约在武则天时弃官后游于维扬一带,留下了《渡瓜步江》一首,其中吟有“……月迥寒沙净,风急夜江秋……”让我们便能领略到码头连江,风急浪涌之景象。孟浩然在扬州辞别友人薛八。临行题诗惜别:“……广陵相遇罢,彭蠡泛舟还。樯出江中树,波连海上山……”扬州通江的捷径,唯瓜步与瓜洲。从“樯出江中树”一句解读,孟浩然所乘的舟船,应自瓜洲启航,所以他的船出航不久便见到了江波海涛混然渺渺,欲吞山峦的磅礴气势。刘长卿送李端南渡时,这位杭州司马所乘的船只,也是从瓜洲启锚渡江,经京口进入江南运河南行的。诗人在《瓜洲道中送李端公南渡后归扬州道中寄》里叹惜地吟道:“片帆何处去?匹马独归迟。惆怅江南北,青山欲暮时。”帆影在阔港宽江之间很快地消失了,暮色也已降临了。唐僖宗时高蟾的乘舟于夜间靠泊了码头,大约是闲于舱中,题吟了《瓜洲夜泊》一诗。这位御史中丞在此港夜泊的主要感受是:“……一夕瓜洲渡头宿,天风吹尽广陵尘。”港口之大,浪涌涛高,因风的推耸,船在不停的摇晃,由此他感到,风好象一夜之间就把整个扬州的尘土都吹尽了似的。
瓜洲北面的扬子津,见诸许多诗人的题吟之中,是瓜洲港区中最主要的、能够吞纳天下的壮阔码头。最早将它吟入诗中的,是祖咏的《泊扬子津》一诗:“才入维扬郡,……江火明沙岸……”诗人所乘的舟帆,刚进入扬州水域,首先就靠泊于灯火通明的扬子津码头,因为这里是船只航入扬州内港的必经之处。孟浩然诗吟《扬子津望京口》:“北固临京口,夷山近海滨。江风起白浪,愁杀渡江人。”吟江浪如雪、海衔夷山,这正说明瓜洲港区中的这座码头在长江、运河与海路舟船往还的枢纽地位。
记得刘禹锡在他的《鹤欢》二首的序言中,就特别提及到他和白居易曾经在扬子津相遇互诉之事。刘禹锡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由朗州(今湖南省常德县)迁任为夔州刺史,后又于长庆四年调任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他在《别夔州官吏》中辞吟道:“三年楚国巴城守,一去扬州扬子津……”在别同僚述去向时,诗人便迫不及待地说自己首先要去的地方,就是要到扬子津去看看。诗人卢全眼中所见到的扬子津是:“风卷鱼龙暗楚关,白波沉却海门山。……”在江海相接之处,海风和江涛似乎激起了鱼跃龙飞,白色狂澜竟然也似乎要将立于海口的高山吞沉下去,天色也因此而暗然无光。这大约是扬子津变和颜为怒貌的画图。即使如此,船家们却也敢于等闲的弄潮。李绅在《早渡扬子江》里,吟唱他于一个清晓渡江那会儿,恰恰是:“日冲海浪翻银屋,江转秋波走雪山。……”诗人当时急于要去浙西与时任诸道转运使的王播相会,才同舟人一样地视雪山般狂涛于无畏而涉之。可见凡靠泊或航渡过扬子津的诗人们,但见处于江涛海云之中的港津,观感几乎完全相同或相似。正是这种壮观,才是扬子津聚散舟航的大有作为之地。它因与扬州城里的内港相通,江船可经此航入市区,海舶则可在扬州东侧的海陵换船进入城区内港。唐时日本高僧圆仁来华,就是走的这条路线。唐代经海道运往幽燕的军需物资,大都经扬州海港启航。这是杜甫在他的《后出塞》(五首之四)中告诉我们的:“……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与台躯……”
扬州的市肆与城中的内港,是紧紧相依难分的。运河、街市、桥梁似乎是一个立体互通的水郭陆市。诗人姚合有《扬州春词》三首。其一,吟唱扬州“园林多是宅,车马少于船……”扬州虽是港城,可它的住宅却已经园林化了,这正是扬州美的所在之一。城内的交通工具,自然以舟为主。他的《扬州春词三首》之三中描绘的市景:“市廛持烛入,邻里漾船过。……”可见在这里,连邻里之间串门都是荡着兰舟互相往还。罗隐的《广陵春日忆池阳有寄》,让我们更能解知这座城在水中、水在城里的扬州,其水、城、舟、桥诸要素是多么的亲和相容了:“烟水濛濛接板桥,数年经历驻征挠。醉凭危槛波千顷,愁倚长亭柳万条……清流夹宅千家住,会待闲乘一信潮。”除烟柳画桥、碧波长亭等大好景色之外,最堪一提的,是清澈的邗沟两岸那数以千计的街市美宅。待到广陵潮涌入郭内时,大家便驾着画舫信自游去,这是多么快乐啊!这里“清流夹宅”的吟唱,说明了扬州城市,基本上是沿着邗沟运河发展的。宋人沈括在他的《补笔谈》中记说:“扬州……旧城南北十五里一百一十步,东西七里三十步。”此记与罗诗所吟吻合。上世纪80年代,在扬州市内地下5米处发掘出唐代两条南北走向的古河道。第一条古河道有木桥桩33根,分为8排,每排4根,以此推测,河宽约31米,是当时大运河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东35米处的第二条古河道,是当时挖入式港池,供船只调头编队。据《扬州水道记》、《瓜洲志》等史籍的记载,唐时港区的运河中还建有一批斗门,类似于今天的船闸,用以控制水位、调节水流,以便使船只平稳地、不间断地通航。
港口岸上的建设,除建在滨河岸边供过往的官员和旅客们进住的华丽馆驿如迎銮驿、建安驿、扬子驿等之外,更多的是建在码头上的储物仓厫(今天的仓库)。所建的仓房,有的专储漕运余米;有的用来专储新谷等等。扬州港口的这些配套设施,在我国古代水运史上,可称之为最先进的举措。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随着港口业务的日益繁忙,唐王朝首创性地设置江淮转运使,常驻扬州。于是我国水运交通中最早的港务管理机构及港口最高负责人便在扬州诞生了。扬州在当时国际通商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因此,港口还另设有专管外国海舶入境的机构——市舶司,从而结束了唐代以前海外来舶的自流状态。
蜚声全国的扬州手工业,以造船、制盐、制茶、制药、纺织及铜器制造为主。扬州出产的铜器,品种之多,数量之大,在全国无与可比。这里,我们且引《杂曲歌辞》中之《得体歌》证之:“得体纥那也,纥囊得体那。潭里船车闹,扬州铜器多。三郎当殿坐,听唱得体歌。”歌中的“三郎”即指玄宗李隆基。唐天宝初年韦坚以陕郡太守之职任水陆转运使。在任期间,他在长安的浐水之滨兴工开凿了广运潭,专门纳泊吴会数十郡舟楫运来的冶铜宝器。可见扬州制造的锦镜及铜质宝器之优胜,居吴会之首。一时间,江南数十郡的朝贡舟船,连绵不断地经扬州航达长安,聚泊于广运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