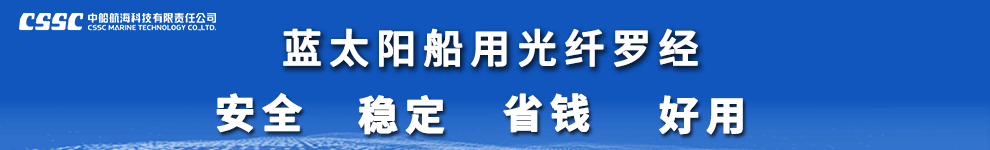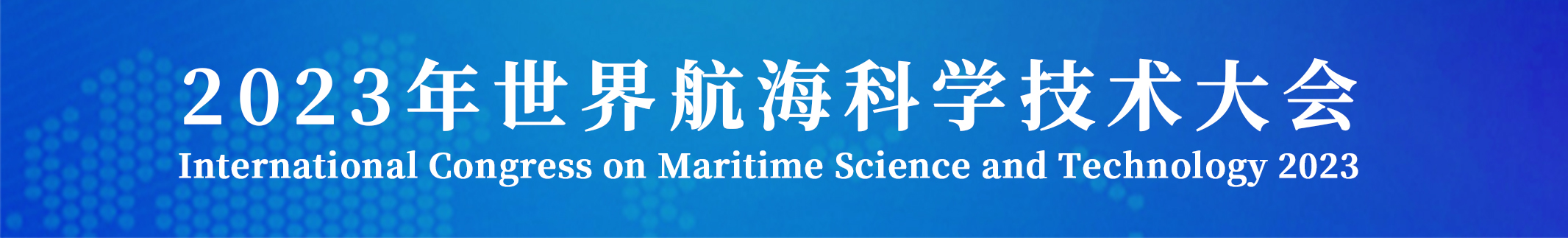沙船:尘封的上海历史文脉
沙船的由来
《宋史·兵志》有“防沙平底”船的记录,《元史·食货志》有“平底海船”的记载。乾隆《崇明县志》说:“沙船以出崇明沙而得名,太仓、松江、通州、海门皆有。”可见沙船与上海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
在元代北洋航线的开辟中,也能见到沙船的身影。元代因汴水干枯,黄河改道,南粮北运受阻。至元十九年(1282年),朝廷命朱清与管军总管罗璧负责建造平底海船60艘,装运漕粮四万六千石至京师。此次航行冬季从太仓刘家港(今浏河)出发,次年三月到达直沽。因为是初次北航,所以路途困顿,沿山求屿,凤信失时,航程极长。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朱清又开辟了新的北洋航线,航程开始缩短。第二年,他们又发现更加便捷的航路,航线从刘家港出发,经过崇明三沙出海,过黑水洋、成山、刘公岛、登州、沙门岛,在莱州洋面进入界河。凤信有时,从上海出发到京师,不过旬日。从上海到天津的海上路线,在元至元年间就有从刘家港开船,经海门的廖角咀放洋,再北航至山东成山角西折,过刘公岛达于天津,全程约4000余里。 后人魏源在评论前人的这些航海壮举时说:“海舟不畏深而畏浅,不患风浪而患沙礁。江南沿海,横亘五大沙,舟行所最畏。元初沿海求屿,逾年始至,旋避其险,径放大洋,而旬余即达。”
沙船的名字正式出现在明代,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成书的李昭祥著《龙江船厂志》卷二“舟楫志”中,已经记有“二百料巡沙船”的较详细制造规格:“船面自头至梢六丈一尺,船底自头至无板处四丈,无板虚梢一丈一尺六寸。头阔七尺五寸,深四尺一寸,中阔一丈二尺三寸,深四尺二寸,梢阔九尺四寸,深五尺。”料是古代计算木料的一种计量单位,一根两端截面为一平方尺,长度达到七尺的木材为一料,可见二百料的巡沙船是一种相当大的木帆船。在明代万历年间(1573-1615)成书的王圻等著《三才图绘》中,第一次出现了沙船的图像。
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康熙颁布了废除海禁的命令,以前被禁锢的沿海运输贸易得以再度发展。南北沿海新航路的航船从浏河口改泊吴淞口。翌年上海设立海关,沙船就进泊到黄浦江,上海日益成为沿江和沿海航运的中心。从北洋运来上海的货物主要是豆、豆饼、油、小麦,以及梨、枣等土产,从上海运出输向北方的货物,主要是棉布、棉花、丝织品、茶叶等,还有南方生产的糖、纸、茶叶、胡椒、海产等。所以上海人民中早就有“沙船之集上海,实缘布市”的说法。
那时,北方关东的“豆、麦每年至上海者千余万石,而布、茶、各南货至山东、直隶、关东者,亦由沙船载而北行”。以至北方生产的“粮、豆、枣、梨运来江浙,每年不下一千万石”。由于沙船运送的货物大宗为关东的豆麦,所以沙船又称豆船。上海在乾隆年间,港口已经相当繁荣。城东门外号称“舳舻相衔,帆樯比栉,不减仪征、汉口”。“往来海舶,俱入黄浦编号,海外百货俱集”。
上海商船会馆的兴衰
沙船业是从元代海运漕粮开始在上海兴起的行业。随着东南沿海贸易的恢复,以沙船为主体的航运业得到迅猛发展。上海号称有“海船数千,梢水数万”(明嘉靖《上海县志》),成为沙船集聚地。沙船业促进了上海城市兴起和经济繁荣,并且孕育了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1990年公布的上海市市标中,图案中心扬帆出海的就是沙船,它象征着上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
沿海南北远距离的商品交易,既繁荣了北方的市面,同样也给上海城镇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一批批关东和山东的商人来上海开店分销北方货,共同的商业利益就为北方商人建立地域性的商帮组织提供了条件。
繁荣的沿海南北贸易也催生了一批新兴的沙船主,像康熙时期的船商张元隆。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船户张元隆呈称:“有自造贸易沙船一只,领本县上字七十三号牌照,于本年六月初六日装载各客布匹、瓷器,货值数万金,从海关输税前往辽东贸易。” 后来,张元隆很快就在沙船经营中发达,滚滚而来的财源刺激了他扩大投资沙船业的意愿,“闻其立意要造洋船百只”。
其中,乾隆年间以朱氏、嘉庆年间以郁、王、孙三姓称首富。王文源、王文瑞兄弟开设“王利川船行”,拥有沙船百余艘,在小南门外建有王家码头。道光、咸丰年间是上海沙船业鼎盛时期,当时有史可查的沙船商号有30余家,其中最有名的有王永盛、郁森盛、沈义生、王公和、李久大、郭万丰、经正记、萧星记等。
沙船的出现提升了海上运输能力,满足了当时沿海南北物资交换的需要,推动了区域商品市场的形成。从上海城镇商品市场来看,沙船运输业推动了豆业、钱庄等行业的发展,对上海城镇的商品经济发展起到助推器的作用。
随着外国航运势力大举入侵。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入港外籍船舶44艘,吨位0.86万吨; 道光二十九年133艘,5.25万吨; 咸丰三年(1853年)437艘,15.72万吨;咸丰八年已达754艘,24.26万吨。外国商船不仅装备和技术先进,而且有不平等条约庇护,构成了对沙船为主体的中国旧式航运业的严重威胁,“轮船畅行,华船利为外夺,以致沿海船商寥寥,船商生计顿蹙”(《刘坤一遗集》)。还有少数外国商船恣意掳截沙船等中国木船,掠劫货物。
同治八年,恭亲王奏称:“上海沙船从前极旺,一经洋商装豆石,遂使数千只沙船尽行歇业,数百万家资之船户,亦为贫民,其舵工水手,更无生计”(同治《筹办夷务始末》)。上海街头时而可见沦为乞丐的原沙船水手。此时,上海地区沙船已由二三千艘锐减至不足四五百艘。一部分沙船商以“诡寄洋商”(将船所有权转外商,以外国商船名义经商)方式勉强维持。也有部分沙船商(如朱家)投资于外国商船。以后随着近代轮船的兴起和沿海定期航班及不定期货运的开设,沙船业更趋清淡。
留住沙船文化的根
上海环航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春阳先生是活跃在长三角地区的航海文化传播者。他特别对上海沙船文化一往情深,致力于"上海沙船文化节"的申报,还向政府有关部门上报了把崇明建设成为"沙船文化休闲体验岛"的提案,渴望获得行业的认可和支持。张春阳先生认为,中华古代造船与航海史上开拓性的创造与发明,是中华文明史、世界文明史中辉煌的篇章。人类海洋文化形成的"基因"。
近日,记者跟随着张春阳先生的脚步,走进他的船舶工作室,各式各样的古船模型让人目不暇接,一艘仿制的沙船他尤为喜爱。
张春阳先生是一个生长于黑山白水之间的汉子,为何痴迷于古船与航海。
张春阳先生娓娓道来:“少年时一段尘封的记忆可能是诱因吧! 1970年,我随父进‘五七干校’,被遣送到渤海渔村。出海的三年中,经历了一次险情。我结识了海洋,体会了舟船,感知了航运。2004年,我回到上海,学习了解了从一艘古船到形成一个产业,进而催生一个大型港口城市的上海沙船文化。尘封了30多年的 ‘人船与海洋’的情结得以释放,激励我研习上海沙船文化的独特魅力,痴迷至今。”
环顾四周陈列的精致船模,记者询问:“这里只是古船模型的制作吗?”
张春阳先生答道:“古船模型的制作只是公司出品的文化商品中的一个种类。我们公司追求的目标,一是社会效益,尽其所能传播中华祖先的造船、航海文化,提升国民海洋、海运、海权意识,为今天中国实现海洋强国复兴梦输送励志奋进的文化动力;二是经济效益,坚持不懈地研发设计船模型新品,研发设计古代海洋文化主题的观展新模式,研发设计青少年、学生习作的学材包、资源包,以及教学用的实型教具、教材,策划设计承办有关名人、名史、名船之类的海洋文化活动项目。很希望在梳理、策划、建设沙船文化体系的上海城市文化建设中有参与的机会。”
张春阳先生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习古思今”的思想,是告诉我们中华文明宝库永远是中华民族图强向上的思想库。沙船文化史中展现给人们的中华领先创新、开拓奋进精神,对于今天的中西文化汇集,实现“中国梦”的先行城市——大上海来说,更是思想层面、文化层面的“中流砥柱”。
关注沙船文化的不止张春阳一人,上海历史博物馆原馆长潘君祥也是同道中人。
现在,有着300年历史的会馆仅保留了正门、戏台以及戏台面对的正殿,原来正殿南北的配殿已经看不到了。正殿和戏台部分结构残缺不全,门楼上的题字难以辨认,亟须加以修缮。“上海商船会馆是上海港口城市发展重要的历史文脉,也是一处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希望更多的人去关注和保护它。”潘君祥呼吁道。
上海历史博物馆原馆长潘君祥表示,沙船和商船会馆在上海航运历史上的作用不容置疑。上海市的市标中设计了一艘五帆沙船,就是对沙船海上运输业历史贡献的一种肯定。沙船和商船会馆清晰记录了上海航运发展史,鉴于商船会馆的重要历史地位,1987年会馆的建筑被列为上海市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