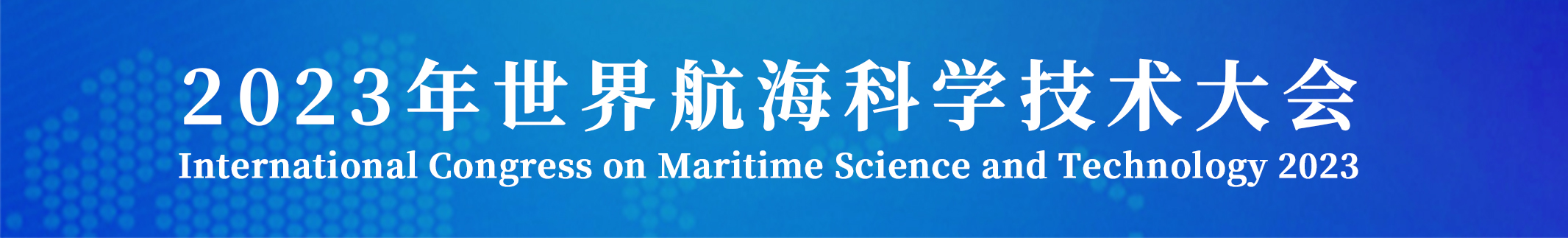索马里边境走访手记:像水一样吧,我的朋友
在一个晴朗的11月午后,索马里籍记者穆赫亚丁·艾哈迈德·罗布勒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某咖啡厅里眯缝着双眼,回忆起在老家摩加迪沙时的岁月。从2007年逃离那个战火纷飞的城市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家人。穆赫亚丁说,他想起了1993年10月3日,美军一架黑鹰直升机坠落在村子里以后,他的妈妈紧紧地拉起他的手,一个劲地向外跑……说着说着,他突然从回忆中抽离出来,毫无征兆而又充满好奇地问我:“告诉我,怎么你们中国人跟谁都不结仇呢?”
我一时没答上来。此前,我们正在讨论索马里社会对该地区内西方霸权(尤其是西方干预)的普遍不信任和仇恨。这种怨念是如此之深,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极端主义暴力,并将索马里引入了其所处的困局——各大洲的教科书上都会如此形容它:“一个可憎的、危险的、失败的国家”。
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正如毛泽东所说:“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多年来,各索马里人社区都致力于将一个基本的事实公之于众,即外国政府及舰船乘索马里陷入长期内战之机,在该国沿海进行大规模非法捕捞,并向其海滩上倾泻了数量惊人的电子垃圾和核废料。这些对当地海域资源不可逆的摧毁,使索马里渔民彻底失去了自力更生的机会。他们中的一些人于是被迫诉诸于暴力,并最终成为海盗或海盗的同情者。
这并不是要把海盗的存在合法化,也不是说作为一种自发反抗的形式(至少在其起始阶段是这样),索马里海盗的出现对各个受剥削的沿海社区有什么革命性的、解放性的意义。但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对各外部势力长久以来给当地资源造成的不可逆转的掠夺漠然处之,又是什么让他们对不只是海盗,而是全体当地人民指指点点,仿佛这些本土群众生来暴力,只知和各外国友人(其“善意”往往被无限拔高了)持枪相向?
人们都对未知充满恐惧。但在天翻地覆的过去一个多世纪里,中国百姓对索马里人正在面临的种种指责早已经耳熟能详了。在短短几十年前,中国还处于被西方以革命的名义妖魔化的阴影之中;即便是今天,中国也仍然无法摆脱另一种,被以扩张的名义妖魔化的阴影。
而那些近年来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去土地的中国农民(在扶助政策缺失的情况下,其中的部分群体也显示出了日渐暴力化的趋势),对被剥夺了生产资料的索马里渔民的处境,也多少会感同身受。
这可能正是中国人“跟谁都不结仇”的一个根本原因。中国之大、之复杂,决定了其文化的本质必须是多元的。“和而不同”的观念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根基(孔子说,“同而不和”的是“小人”)。多少代中国人都是在这种不命令、不强迫、不假定的哲学下成长起来的。
在各种乱相频生、文化冲突加剧的当前世界里,这种观念的意义是:互不干涉的政策导向、开明和聆听的意愿,以及助人于危难之中的胆识。
不论以哪种标准考量,中国都绝不完美。但难能可贵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都一贯坚持着如是立场。我对能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而感激不尽。
每个知道我要独自前往内罗毕东利区和东北省曼德拉镇的人都建议我不要去。曼德拉是肯尼亚、索马里、埃塞俄比亚三国的交界处,一片非索马里人不愿踏上的土地。人们告诉我,“这些地方都很危险,(相对当地居民而言的)‘白人’是从来不去的。”
但我的问题是:我们凭什么认为这些被孤立地区内数百万贫穷的百姓就是“危险”的呢?既然这些人能按其方式生活,我们怎么就不能尝试着做同样的事呢?我们怎么就不能走到他们当中去,微笑着与当地人和平相处呢?
我在肯尼亚采访的九天里,遇到的多数人都无比友善 ——我为此感谢宽容豁达、与人为善的东方哲学。